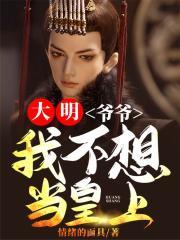笔趣阁>家族崛起:从当爷爷开始 >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章尔等是何人(第1页)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章尔等是何人(第1页)
就这样,狐族加入了白玉京。
加入的过程很简单,杨正山让苏媚在灵源之地挑选了一块福地,然后苏媚将青原洞天的门户安置在福地中,如此灵源之地就与青原洞天有了连通的通道。
当然,杨正山也在仙宫内给。。。
雪线在晨光中缓缓后退,像一条疲惫的蛇蜷缩进山脊阴影。林知微离开共情塔已满三月,她的足迹并未停歇于北方石殿的觉醒,也未止步于启言镇心语庭的奠基。她知道,真正的沉默不在荒原,而在人心深处那些被磨平棱角的角落??那里长年不见阳光,连回音都会腐烂。
这一日,他们行至中陆废墟带边缘,一座名为“哑城”的旧都遗址。这里曾是心契文明最辉煌的学城,千年前因一场思想清洗而遭封禁,整座城市被施以“言蚀咒”,所有文字自动风化,声音传播不出百步即消散。传说中,最后一位公开演讲的哲人在此地讲完最后一课后,张口却发不出任何声响,只能用指尖在石板上划出“我仍在说”四字,随即倒地而亡。
如今城墙早已坍塌,唯有中央高台尚存,台上立着一尊无面雕像,双手捧书,但书页空白如新雪。
“我们不该来。”老水手低声说,他耳朵上挂着一枚从悔音号残骸打捞出的骨铃,此刻正微微震颤,“这地方……吃声音。”
林知微不语,只是轻轻摘下背上的竹笛。她没有吹奏,而是将笛身贴在唇边,任寒风吹过孔隙,发出细微呜咽。刹那间,地面浮现出无数裂纹般的蓝光,如同蛛网蔓延向四面八方。那些光纹所经之处,尘土翻涌,竟有细小的纸片从地下钻出??那是被掩埋千年的笔记残页,上面字迹模糊,却仍可辨认出断句:
>“若真理不能言说,则谎言将成为律法。”
>“孩子们开始模仿大人的沉默。”
>“今天,我又删掉了第三封信。”
少年言愈师蹲下身,指尖轻触一页碎纸,忽然浑身一震。他虽天生失语,但能以画笔勾勒他人情绪轮廓。此刻他迅速抽出随身画板,炭笔疾走,勾勒出一幅幻象:无数人影跪坐在黑暗大厅中,每人嘴上缝着银线,而头顶悬浮着一张张飘动的嘴,正在代他们说话??那些嘴说着赞美、忠诚、顺从,却没有一张属于他们自己。
“这不是历史。”他用手语告诉林知微,“这是现在。”
林知微闭目,感知如根须深入大地。她“听”到了这座城真正的声音??不是亡魂哀鸣,而是活人仍在重复的压抑。每一个踏入此地的人,无论来自何方,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音量,回避敏感话题,甚至忘记自己原本想说什么。这不是诅咒残留,而是集体心理创伤形成的“沉默场域”,它像霉菌般附着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莫问走到她身旁,低声道:“你打算唤醒它?”
她睁开眼,目光沉静如深潭。“不是唤醒,是打破。”
当夜,他们在高台下扎营。林知微取出爷爷留下的竹笛,又从怀中掏出那片干枯的灯莲花瓣,轻轻放在掌心。她对着花瓣低语:“你说声音已种下,可有些种子,困在冻土里太久。”
风起,花瓣微微颤动,仿佛回应。
次日黎明,林知微独自登上高台。她在无面雕像前盘膝而坐,将竹笛横置膝上,却不吹奏。相反,她开始说话??很轻,很慢,像是怕惊扰什么。
她说起了阿澈。
说他在九钟之下如何选择自我分解,只为留下一个“倾听的锚点”。
说他临终时眼中没有恐惧,只有遗憾??因为他再也无法亲口告诉她:“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她说起了爷爷。
说他一生装作普通农夫,在田埂边吹笛哄孙女入睡,实则每夜都在用笛声安抚躁动的地脉,防止心源石暴动伤及村民。
说他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的不是遗嘱,而是叮嘱:“别怕吵,孩子,世界需要难听的声音。”
她说起了自己。
说她三十年来替千万人听见痛苦,却从不敢承认自己的悲伤。
说她曾在共情塔顶听着别人的哭诉彻夜难眠,却从未为自己流过一滴泪。
说她以为沉默是慈悲,后来才明白,那是怯懦。
每一句话落下,地面蓝光便黯淡一分。雕像脚下开始出现裂缝,从中渗出黑色雾气,凝聚成人形轮廓,似要扑向她。但她不停,继续说着。
她说起流浪汉。
说他做出那支一模一样的笛子,并非巧合,而是血脉共鸣让他梦见了传承仪式。
说他本可成为新一代守护者,却因出身卑微被驱逐出学城,最终冻死桥洞,手中仍紧攥着未完成的笛胚。
说到此处,黑雾剧烈翻腾,化作一道嘶哑吼声:“闭嘴!你不该提这些!”
林知微抬头,直视那团扭曲光影:“为什么不该?因为羞耻?因为难堪?还是因为你们怕一旦说出来,就再也无法假装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