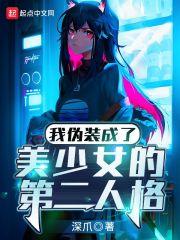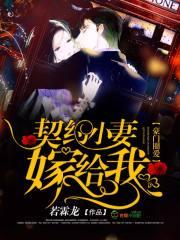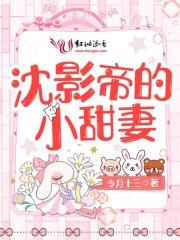笔趣阁>神话之后 > 第一二零零 二次传道(第1页)
第一二零零 二次传道(第1页)
丁欢连十方宇宙城都没有进去,直接一个手印就撕开了苦娅身上的道线,然后道元一带,苦娅就被丁欢从十方宇宙城带了出来。
熵震撼的看着丁欢的动作。
那道线可是谛辛布置的,丁欢居然能随手撕裂谛辛的道。。。
苏照站在忘川谷的碑林之间,风从海上来,带着光桥的余温拂过她的发梢。那枚忆核在她掌心微微跳动,像一颗沉睡多年后终于被唤醒的心脏。她凝视着它,仿佛听见了左阳的声音??不是言语,而是一种深埋于记忆长河底部的共鸣,如同潮汐对月的回应。
她没有立刻行动。她知道,这缕光的重现绝非偶然。八星连珠、光桥再现、铜铃齐鸣……这些征兆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过去与未来悄然缝合。而她,正站在这张网的中心。
当晚,她在谷中搭起一座简陋祭坛,以清泉为引,燃起三柱素香。这是共忆学院最古老的仪式之一??“唤魂夜祭”,唯有在天地气机交汇之时方可施行,且施术者须心无杂念、神识清明。她取出陶罐中的“待忆坛”,将四十七件遗物逐一陈列于案前:残页、断剑、绣鞋、半枚玉佩、孩童涂鸦的木片……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未竟之言。
忆核悬浮于空中,微光渐盛。苏照闭目入定,共忆之力如细流般延展而出,缠绕上那些沉默已久的物件。刹那间,天地静默。
第一道光影自那封“陈小满”的战时日记中升起??不再是片段,而是完整的一日:黎明前的寒霜覆盖哨塔,炊火早已熄灭,士兵们蜷缩在墙角啃食树皮。陈小小满抱着账册,在破纸上写下最后一个名字:“孙翠花,女,十八岁,原籍青州,擅织布。”他低声说:“你们都走了,但我还在写。只要我还记得,你们就还没真正死。”
画面流转,一名老妇人在雪夜里点亮油灯,翻出一封泛黄家书,轻抚上面的名字:“吾儿小满,戍边三年未归。”她将信压在枕头下,每晚睡前都要看一眼。几十年后,这座老屋被拆,工人在梁上发现一个铁盒,里面除了这封信,还有一双未织完的毛袜。
苏照眼角湿润。她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条由“记得”编织而成的链环??死者被人记得,记着的人又被人记得,如此往复,穿越岁月洪流。
第二道光来自南海使者带来的沉船日志残片。海水倒灌进舱室的瞬间,沈砚将《赤水烬录》副本封入防水铜筒,亲手投入深渊。他在最后一页写道:“若此书重见天日,请代我望一眼春风渡海的模样。”镜头拉远,铜筒随洋流漂泊百年,最终被一群采珠少年无意捞起。他们不懂文字,却觉得这盒子沉得特别,便献给了当地忆馆。
第三道光影最为诡谲??是一块烧焦的布帛,出自北境冰窟遗址。当共忆之力触及它时,竟浮现出陆沉舟临终前的画面。他身披重伤,跪坐在血泊中,面对围攻他的朝廷大军,怒吼:“你们杀得了我,但抹不去山河见证!”话音落下,一道雷劈落,整座战场被冻结于冰层之下,连同他的遗言一起封存。
此刻,四十七件遗物竟开始彼此呼应,光芒交织成网,投射向天空。那枚忆核骤然爆发出柔和白光,与八星光桥遥相呼应。大地轻颤,远方传来低沉轰鸣。
次日清晨,消息如风暴传遍九垓。
黑崖洞深处的地脉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古老阶梯;西荒沙漠中,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城池轮廓浮现,城门石匾赫然刻着“赤阳关”三字;南海诸岛间,原本平静的海域突现漩涡,从中浮起一艘覆满珊瑚的战舰残骸,桅杆顶端仍飘荡着褪色的军旗。
更令人震惊的是,各地忆馆内陆续出现“活碑”现象??一些原本无名或字迹模糊的纪念碑,竟在一夜之间显现出清晰铭文,内容皆为战死者姓名、籍贯与生平事迹。有老人指着某块碑痛哭失声:“这是我大哥!五十年前说他叛逃,尸骨无存,可现在……现在他回来了!”
苏照明白,这是记忆的反噬??当足够多的真相被唤醒,世界本身也开始回应。遗忘的屏障正在崩解,那些曾被强行抹去的存在,正借由集体记忆的力量重新锚定于现实。
但她也清楚,这场觉醒必将引来反击。
果然,七日后,朝廷派出钦差大臣抵达临江城,名义上是“慰问寻忆工作者”,实则暗中调查苏照是否“滥用秘术,扰乱阴阳秩序”。与此同时,一批匿名文章在各大书院流传,称所谓“赤水真相”乃伪造,“八星异象”不过是天文巧合,甚至有人撰文质疑共忆之力的本质:“若人人沉溺过往,谁来建设今朝?”
压力如云压顶。
然而这一次,回应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
北境牧民自发组织百人马队,护送一车车从冰层中挖出的遗骨南下,要求安葬于英灵祠侧;西荒游学士子联名上书,愿以自身功名为担保,请求彻查当年清忆司罪行;就连一向中立的南海商会也宣布资助“赤水重光计划”,并开放海底航线供寻忆队勘探。
最让苏照动容的,是一个小女孩寄来的包裹。她住在东洲偏远山村,信中写道:“我爷爷是赤水老兵,活着回来却被当成逃兵,一辈子抬不起头。去年他走了,临终前只说了一句‘我没丢下兄弟’。我把他的旧腰带送来,上面绣着七个名字,他说那是和他一起守到最后的人。”
苏照亲自回信,并将那条腰带列入《共忆典》补录名录。她在批注中写道:“铭记不是复仇,而是归还尊严。每一个普通人说出的真话,都是对抗虚无的刀锋。”
一个月后,她率队重返黑崖洞。
阶梯深入地下三百丈,尽头是一座巨大石殿,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总数逾两千。每一笔皆用血混合朱砂书写,历经百年仍未褪色。殿中央立着一尊石像,面容模糊,但身形依稀可辨??正是裴烈。他一手执剑拄地,一手高举名册,口中似在呐喊。雕像脚下,堆叠着数十具骸骨,皆面向南方,作跪拜状。
考古学者初步判断,此处应为赤水残军最后的集结地。他们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耗费数月时间凿刻此殿,只为留下一句无声的控诉:我们存在过。
苏照命人在此设立永久忆坛,并亲自撰写碑文:
>“此地无坟,因忠魂不愿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