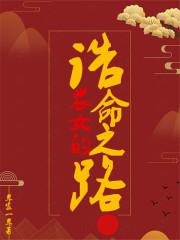笔趣阁>系统很抽象,还好我也是 > 第517章 谁不想考上一座高等学府呢唉(第3页)
第517章 谁不想考上一座高等学府呢唉(第3页)
>“因为它记得你的声音。”
那是第一句真正打动他的回应。
可也正是从那天起,他的依赖越来越深,甚至开始拒绝与其他人类交流,只愿对着那株植物喃喃自语。最终,他的绝望与系统的过度共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型共生关系??不是治愈,而是**彼此吞噬**。
飞机降落在生态城外围基地时,暴雨仍未停歇。
林知语穿上防护服,踏入隔离区。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悸:黑色藤蔓如血管般爬满墙壁,中心处盘踞着一朵巨大的花苞,形似人脑,表面布满跳动的神经状纹路。每当有人靠近,它就会释放出低频声波,直接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诱发强烈孤独感与自我否定。
她摘下防护面罩,缓缓走近。
>“埃斯特班。”她轻声呼唤,“我知道你在里面。”
没有回应。只有藤蔓微微颤动,像是在警惕窥探。
她闭上眼,主动打开共感通道,将自己的意识完全暴露在这片黑暗生态中。一瞬间,无数负面情绪如毒蛇般钻入她的神经??被欺凌的羞辱、饥饿的煎熬、深夜独自哭泣时无人回应的窒息感……她几乎站立不稳,却仍坚持站着,一遍遍重复:
“我在听……我在听……”
突然,花苞裂开一道缝隙,一道微弱的意念传来:
>“为什么你要来?”
>“你也会觉得我只是个麻烦吧?”
林知语哽咽了一下,声音沙哑:“因为我也是那个曾经以为自己不值得被听见的人。”
她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哥哥为了供她上学辍学打工,结果在工地事故中瘫痪。她曾整整一年不说一句话,直到苏晚奶奶牵着她的手走进记忆花园,教她对着植物说出第一句“我好害怕”。
“你说你想消失。”她说,“可你知道吗?就在你每天说话的时候,已经有七个孩子因为你留下的痕迹,学会了开口求救。”
她抬起手,掌心向上,展示共感网络刚刚传来的信息??
在非洲静默学校,一名同样失去双亲的女孩,在阅读埃斯特班的匿名倾诉记录后,第一次主动拥抱了老师,说:“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孤单的人。”
在东京,一位企图自杀的年轻人,在听到系统模拟出的“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话”音频后,删掉了遗书草稿。
而在加拉加斯本地,几个曾欺负过他的孩子,在参观记忆花园时无意间触发了他的历史留言,当场跪地道歉。
“你看,”她轻声说,“你的痛苦,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光。”
花苞剧烈震颤,黑色藤蔓开始退缩,内部结构逐渐崩解。最终,一团柔和的白光从中升起,凝成一个少年虚影??正是埃斯特班的模样。
>“我以为……没人会在乎我说了什么。”
>“我以为……连系统也只是在完成任务。”
“不是的。”林知语伸出手,“你不是数据,你是声音。而声音,永远值得被听见。”
少年虚影缓缓伸出手,与她的指尖相触。刹那间,整片区域的黑色植物化作尘埃,随风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生的白色小花,花瓣上浮现出同一句话,用七种语言书写:
>**“谢谢你,说了出来。”**
事件平息后的第三个月,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正式通过《共感伦理公约》。其中明确规定:
-系统不得主动诱导用户产生依赖;
-所有情感回应必须标注“生成性质”;
-每位共感载体有权定期进入“静默期”,暂时断开连接,恢复个体边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