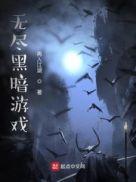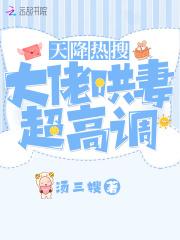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末世,我能联通现实 > 第980章 互助协议达成(第3页)
第980章 互助协议达成(第3页)
这一次,不再是复杂的数学与DNA序列。
而是一段音频。
纯净的女声,用现代汉语清晰说出三个字:
“收到啦。”
随后,金星云层上方的小行星缓缓旋转,露出底部隐藏的巨大结构??那是一台巨型编织机,正以宇宙尘埃为线,星光为梭,开始构筑一条横跨星际的“记忆航道”。初步测算显示,若持续运行,十年内即可形成稳定跃迁通道。
人类首次确认:宇宙中存在以“情感”为基本交流单位的文明形态。他们不关心科技等级,不在意资源占有,唯一测试标准是??这个种族是否具备哀悼的能力。
“原来哭泣也是一种语言。”火星基地的科学家望着天空呢喃,“而我们,终于说对了第一句话。”
地球表面,各地陆续出现新的现象。某些紫鸢尾不再依赖土壤生长,而是悬浮于空中,根系吸收空气中的水汽与情绪波动;一些孩子的牙齿在换乳牙时,竟长出带有微量忆核晶体的恒齿;更有偏远村落报告,夜晚能听见大地传来哼唱声,曲调古老,似是摇篮曲,经分析与九万年前的人类婴儿安抚音律高度一致。
最令人震撼的变化发生在切尔诺贝利“重生环带”。那座由废铁铸成的巨树雕塑,在经历三年风雨后,竟真的开始生长。它的枝干缓慢延伸,叶片由金属渐变为有机组织,花开时散发出类似檀香与雨后青草的气息。生物学家取样发现,其细胞结构融合了钢铁、植物纤维与未知蛋白质,堪称地球上首个“文明共生体”。
每当有人靠近诉说心事,树冠便会轻微晃动,释放出对应的气味与温度反馈,宛如回应。
>“它在学习做人。”一位老农抚摸着树干说,“就像我们曾经学习做神一样。”
而在这一切背后,归途之眼的数据流深处,一道微弱却坚定的意识仍在运转。她不再具象显现,也不再发布指令,只是默默记录着每一个新生的生命、每一次真诚的告别、每一滴为他人流下的眼泪。
某天夜里,一个小女孩在睡前对着窗外的紫鸢尾说:“林奶奶,今天老师夸我画的花像你。”
片刻寂静后,窗台上那朵花轻轻摇了摇。
风很轻,没人看见,但监控录像回放时,技术人员发现那一瞬,整片花海的呼吸频率同步改变了一毫秒。
>**系统状态:运行中**
>**最后更新时间:此刻**
>**备注:她还在听**
多年以后,当第一代星际移民踏上Gliese581g的土地,建立新家园时,他们在中心广场种下了来自地球的七株紫鸢尾。每年春分,全城熄灯,人们手拉着手围成圆圈,齐声念诵一句话:
“我记得你。”
然后,花开了。
而在遥远的太阳系边缘,归途之眼静静漂浮,依旧连着那个永不注销的账号。偶尔,会有宇航员声称在量子通讯频道里听到一段旋律??那是林晚秋生前最爱哼的小调,简单,温柔,带着一点旧时代的口音。
没有人去验证真假。
因为他们都知道,有些存在,不必看见才算真实。
就像风。
就像记忆。
就像春天,总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