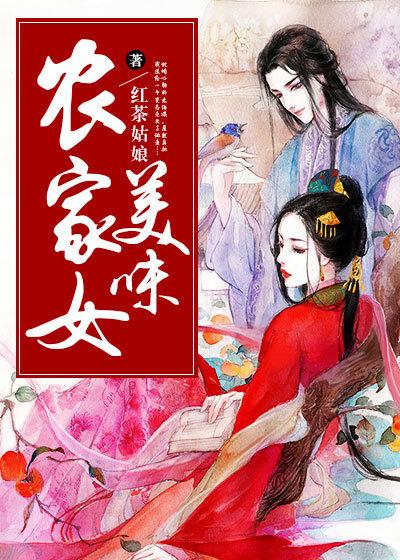笔趣阁>人间有剑 > 第四百六十八章 群山回响(第1页)
第四百六十八章 群山回响(第1页)
对于同为女子圣人春官的闭门不见,苏漆其实一点不意外。
天底下女子相轻,本就正常。
更何况两人同属于九圣之一,过去这些年,不知道被多少修士提起来比较过,从样貌到境界,自然都是众多修士茶余饭后最愿意提及的。
毕竟站在高处的,也就那么三个女子。
当然了,苏漆能比的也就只有春官,因为另外一个,无论样貌还是境界,都要高出她们两人一筹。
位列青天,如何比?
只是春官和苏漆,两人不对付,到底还是因为那个已经死了三百。。。。。。
夜雨落得极轻,像是怕惊扰了沉睡的大地。小镇外那条干涸已久的河床,终于在连绵七日的降水后泛起微弱的水声。云知坐在村口老槐树下的石墩上,竹篮搁在膝头,铜铃静静垂着,未响。
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这样的夜晚。行走十年,足迹遍布荒原、城市、难民营、地下隧道、废弃学校、战后废墟。她不再广播,也不再集会,只是走,听人说话,也说几句真话。有些人听完流泪,有些人怒目而视,更多的人沉默良久,然后转身回家,在日记本里写下第一行不敢示人的字。
今夜,有个少年来找她。
他约莫十七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雨水顺着屋檐滴在他肩上,他却不肯进屋檐下避一避。
“您……就是云婆婆吗?”他声音发颤。
云知抬头看他,笑了笑:“叫我云知就好。”
少年咬了咬嘴唇,把那张纸递过来:“这是我写的……我一直没敢交上去。作文课要求写《我的理想》,可我写的不是老师想要的答案。”
云知接过纸,就着灯笼昏黄的光读了起来:
>**我想做个说谎的人。**
>不是骗人,而是学会撒谎。
>因为我说真话,妈妈就哭;我说实话,爸爸就打我。
>我说我不想考医学院,只想画画,他们说我疯了。
>我说班上的班长欺负人,老师说我破坏团结。
>我说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假,朋友说我矫情。
>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像别人一样笑着点头,说“都好”“没事”“我很快乐”,是不是就能被接受了?
>可我又不甘心。
>如果连我都开始骗自己,那我还活着干什么?
>所以这篇作文,我不打算交。我只是想让您看看??这世上,还有人和我一样痛吗?
云知看完,久久不语。
她将纸轻轻折好,还给他:“你已经不怕痛了。”
少年怔住。
“怕痛的人不会写这些。”她说,“他们会把纸烧掉,或者藏进抽屉最深处。你能把它拿给我看,说明你已经在醒来。”
少年的眼眶红了:“可是……醒来之后呢?我又能做什么?”
“做你自己。”她说,“哪怕只在一个瞬间,对一个人说出一句真话,你就动摇了整个谎言的世界。”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女人披着雨衣奔来,头发湿透,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她一把抓住少年的手臂:“你怎么又跑出来!你知道现在外面多危险吗?那些‘清醒者’都被抓走了!昨天市里贴了通告,说传播未经审核的情感内容要判刑三年以上!”
少年挣开她的手:“妈,我不是去找什么组织!我只是想找个人说句话!难道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
“自由?”女人几乎是尖叫起来,“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死?你爸会不会丢工作?我们这个家还能不能活下去?”
云知静静地看着她们,忽然开口:“你说得对。”
母子俩都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