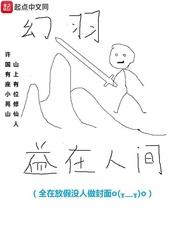笔趣阁>死亡实况代理人[无限流] > 第255章(第2页)
第255章(第2页)
他吓一跳,忙要他们指路,到了庭前时,薛宅子的人几乎都在了。可人群的中心仅摆了个不足一米七长的木箱,里头尽是叫人崩溃的哭喊。
——文侪的声音。
他踉跄一步要上前,没曾想给那凤梅攥了:“你别上去,适才那薛有山都跪下了,也没能把文侪放出来!你上去为他求情,不是又要惹他遭人非议么!”
“我又能怎么办?!”戚檐难得失控,几秒钟后却还是镇静下来,他说,“好,成,小爷我不去给嫂子惹麻烦!我走,我走还不成?!”
他知晓昨夜文侪去翻了他的房间,不出意外,那些线索应该都没收拾。他大步往那儿走,而后在自个儿屋内了解到了自己原身对郑槐的暧昧感情。
“特么的,又来一个疯子!”
戚檐将手中书信反覆看了,总觉得差了些滋味。
他想啊想,不久后想到阴梦里他和文侪二人中的非九郎者,多是影响另一位生死的重要角色。那么假使这二少与他嫂子郑槐仅仅是追求与被追求的关系,郑槐就不该将这薛二少选定为他戚檐的替魂对象。
“应该在哪儿还有些线索……”戚檐推开屋门跑出去,叫外头北风吹得耳朵都没了知觉,“谁才是最有可能掩藏郑槐与二少有私交的人?”
“除了想要拿那般丑闻来要挟人的,便仅剩下想要隐瞒此事的……”
戚檐有预感,那些线索若是不在苗嫂屋里,则必在薛当家和薛母那儿。由于苗嫂和文侪住在同个屋子里,估摸着重要线索文侪早翻了个大概。
他于是朝主卧跑去,只跑得风百次狂掀过,双耳刺啦刺啦地发疼。
***
当家的屋子果真与宅中其他人的级别不同,一进门便是明晃晃的黄花梨木雕,再转眼,是各式各样的小柜、博古架……
戚檐没工夫欣赏,方进屋,便齐开两屉,将里头有用没用的东西都挨个倒出来看过才算完。
他先前听薛宅管事说过,那老爷和夫人平日里脾气还算温和,对待儿子更是一口一个心肝儿,可却不喜欢儿子跑他们房间瞎闹。
由于那提醒过于露骨,戚檐不免也生了些警惕,翻东西时再着急也时不时要往外头瞄个两三眼。
屋里的奇珍异宝十指数不过来,由于那薛当家之前读过点书,为附庸风雅,买了不少书籍作装点,这当然无足轻重,但可苦了扫雷式翻找线索的戚檐。
为了翻到几张郑槐与他原身交流的信纸,硬是将那些大小书籍挨页翻去。
没有。
他却不信。
他的眸光在屋子上下绕了一圈,末了停在一个被列于博古架上的司南上。
眼前忽而不合时宜地闪现起薛有山那块停滞不转的表。
这司南会转么?
他生了那般疑惑,鬼使神差地将司南底盘往另一个方向转去。
那司南果真半分不动。
“时不变,地不动……我们这是被困在了哪个风水宝地?”
戚檐于是抓起那司南满屋子走,从里踱到外,直到那司南在一口水缸前颤悠悠地转动起来。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攥着块石头便如抛掷棒球一般砸向大缸。
砰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