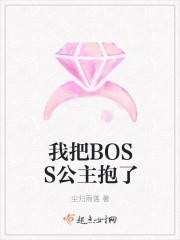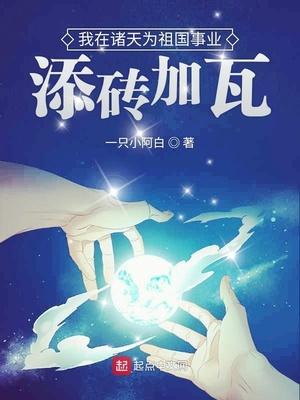笔趣阁>离婚后的我开始转运了 > 第1803章 晚上没空改天再说吧(第3页)
第1803章 晚上没空改天再说吧(第3页)
展览第七天,一名男子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在酒后殴打妻子,看到这里才意识到,她每次求饶的声音,其实都在呼救。我已经去自首,并申请心理矫治。”
第十天,教育部宣布将在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中加入“倾听训练”模块,教材案例源自“回声行动”真实录音(经脱敏处理)。
阿?受邀参与课程设计会议。会上,一位资深教育专家提出疑问:“会不会太煽情?孩子们能承受这么多沉重吗?”
她摇头:“我们低估了孩子的共情力。真正的教育,不是屏蔽痛苦,而是教会他们如何面对它。就像教游泳不能只讲理论,必须让人下水。”
会后,她独自走在长安街上,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手机忽然响起,是朵朵打来的视频电话。
“阿?阿姨!”女孩兴奋地晃着手里的奖状,“我拿到市青少年歌唱比赛一等奖啦!评委老师说我声音里有故事!”
“真棒。”阿?笑着擦了擦眼角,“那你愿意再唱一首给我们听吗?”
朵朵点点头,清了清嗓子,唱起一首原创歌曲:
>“我不是最亮的星,
>也不是最美的风景,
>可当我开口说话,
>世界终于听见了我的姓名……”
歌声通过电波传入耳中,阿?闭上眼睛,仿佛看见无数个曾经沉默的灵魂,正一一醒来。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民政局门口,仍是那天的模样,行李箱轮子卡在台阶缝里。前夫站在不远处抽烟,目光冷淡。
她没有走过去签字,而是蹲下身,打开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对着空气说:
“我叫阿?,今年三十六岁。我刚结束一段婚姻,我不知道未来在哪,但我决定从今天开始,认真听每一个人说话。”
梦里的前夫愣住了,烟灰掉落鞋面也未察觉。
画面一转,她看见“回声车”驶过沙漠、雪原、海岛、高原;看见法庭上法官播放一段孩童录音后暂停判决,询问孩子真实意愿;看见养老院里失智老人听着昔日情书录音,突然握住伴侣的手喊出名字;看见监狱中的施暴者听完妻子录音后伏案痛哭,写下忏悔书……
最后,她站在一片星空下,万千声音如星辰般环绕周身,齐声低语:
“谢谢你听见我。”
她猛然惊醒,窗外晨曦初露。她迅速抓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
>“当我们不再恐惧倾听,治愈才真正开始。”
清晨六点,她群发了一条工作指令:启动“百名施暴者倾听计划”试点,联合司法矫正系统,为家暴犯罪人员提供受害者录音匿名聆听服务,作为心理干预与再社会化的一部分。
有人质疑此举过于理想化,甚至可能引发二次伤害。但她坚持认为:“暴力源于冷漠,而冷漠始于拒绝倾听。如果连加害者都不曾真正‘听见’痛苦,我们如何期待他们悔改?”
三个月后,首批参与项目的23名服刑人员提交心得体会。其中一人写道:“我第一次听她哭着说‘你能不能别打了’,才发现原来她一直叫我‘老公’,哪怕在我举起拳头的时候……我以为她是怕我,原来她还在等我变回当初娶她那个人。”
这份材料被纳入司法部社区矫正改革参考案例。
秋天,“回声行动”获得联合国亚太地区社会创新大奖。颁奖典礼上,阿?没有发表演讲,而是播放了一段五分钟的合成音频??来自全球各地的普通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我想回家……”
“对不起……”
“谢谢你记得我……”
“我还爱你……”
“我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