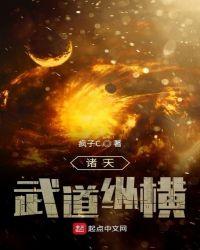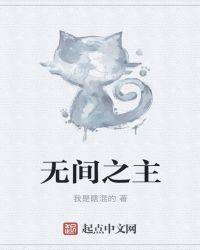笔趣阁>激荡1979! > 第504章 魏明的留学生活(第1页)
第504章 魏明的留学生活(第1页)
第二天,魏明带上彪子一起去思远影业拜访。
之所以带上彪子,是因为昨天吴思远离开的时候,对全场的漂亮女士没有多看一眼,反倒是打量了彪子几眼,他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让彪子晚一天回京,陪自己走一趟。。。。
雨声渐密,敲在窗上如细碎的鼓点。孟波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未落。他忽然想起孙亚男的名字是艾丽娅提过的??那晚她在电话里说:“我父亲的老战友提过一个女炼钢工,叫孙亚男,七十年代在鞍钢出了名,后来调去包头支援三线建设,再后来……就没了音讯。”当时她顿了顿,“她说自己最怕冬天,因为炉火太旺,眼泪一掉下来就结冰。”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孟波心里。他翻出《拾痕录》第一辑的手写笔记,在夹层中找到一张泛黄的剪报:1975年《工人日报》头版刊登的照片,标题为《红炉映丹心》,画面中央是一位戴着防护面罩、手持钢钎的年轻女工,身后熔炉喷涌出金红色火焰,照亮了整个车间。照片下方一行小字:“鞍钢青年突击手孙亚男,连续三年荣获‘五好标兵’称号。”
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消失三十年?
他打开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统协作通道(这是文化部特批的调查权限),输入姓名与出生年月,系统反馈:“查无此人。”他又试了“孙亚兰”“孙雅南”等可能的误录变体,仍无结果。最后他在内蒙古公安厅档案库中检索到一条模糊记录:1983年冬,一名身份不明女性因低温症昏迷于乌拉特后旗边境线附近,送医后苏醒,自称来自东北钢厂,但拒绝提供具体信息,两周后自行离院,去向不明。
时间、地点、职业背景全部吻合。
孟波立刻联系乌拉特后旗人民医院退休医生赵德海。电话接通时已是深夜,老人声音沙哑却清晰:“我记得她。瘦得厉害,眼神却亮得吓人。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炉子灭了吗?’我以为她在说医院暖气,后来才明白……她是梦见炼钢了。”
“她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晚上说梦话,全是操作规程:‘一号高炉加料口堵塞,请求紧急疏通!’‘煤气压力异常,快关阀门!’”赵医生苦笑,“我们那儿连铁匠铺都没有,哪懂这些?可她讲得那么真,就像眼前真有座炉子在烧。”
“她走的时候没留地址?”孟波问。
“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个奇怪的符号,像是个齿轮套着月亮。”赵德海说,“我还以为是胡话,现在想想,会不会是什么暗号?”
孟波心头一震。他迅速调出鞍钢老厂区平面图,逐一对比各个车间标识,终于在第三炼钢厂休息室墙上发现一处涂鸦??正是那个“齿轮绕月”图案。据一位退休工会干部回忆,那是孙亚男所在班组的“精神图腾”,源自她们读过的一首诗:“钢铁不眠夜,齿轮转春秋;愿作炉中火,照破雪疆愁。”
线索重新接上了。
次日清晨,孟波启程飞往呼和浩特,再换乘绿皮火车北上临河。窗外草原辽阔,牛羊如星点散布。邻座是个牧民老太太,听他打听乌拉特后旗的事,忽然插话:“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总穿一件灰布袄,走路有点跛?”
孟波猛地转头:“您见过她?”
“咋没见过?八十年代末她在我们嘎查小学教过几年书,孩子们都叫她‘铁娘子老师’。她讲课特别狠,粉笔头打得准,谁走神就飞过去。但她也最护学生,冬天挨家挨户背娃娃上学,摔断过腿也不歇。”
“后来呢?”
“九十年代初学校撤并,她就走了。有人说去了额济纳旗,有人说是回老家了。但她临走前把所有课本都留在教室,还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字:**火熄了,灯还得亮。**”
孟波眼眶发热。他知道,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沉默的坚守??从炼钢炉前退下后,她把自己锻造成了一根蜡烛。
抵达乌拉特后旗已是傍晚。镇上仅有的招待所只剩一间房,墙上挂着褪色的全国地图,角落用红笔圈了个小点,写着“孙亚男最后出现地”。孟波怔住:这标记不知是谁留下的,竟与他的调查轨迹惊人重合。
当晚,他走访当年经手病例的护士、收留过她的牧民、听过她课的学生。拼凑出的画面愈发清晰:孙亚男并非失联,而是主动切断了过往。她不用真名,不留档案,像一滴水融入沙漠。唯一例外,是每年清明,她都会出现在中蒙边境一座无名烈士碑前,放一束野菊,烧一张写满数字的纸??后来有人偷偷看过,那是1976年某次重大事故中牺牲工人的名单编号。
“她不是忘了过去,”一位老邮递员说,“她是背着它活着。”
第三天黎明,孟波决定前往那座烈士碑。山路崎岖,骑摩托颠簸两小时才到。石碑低矮,被风沙磨平了字迹,唯有基座刻着一行小字:“献给未能归家的人。”草丛里果然有烧纸的灰烬,还有半截铅笔??正是那种工厂专用的硬芯绘图笔。
他蹲下身,指尖抚过焦黑的纸片残角,突然发现背面有一串极浅的划痕,像是用铅笔反复描写的诗句:
>“我不是不想回来
>可我的姐妹躺在炉渣里
>我若安睡,谁替她们睁着眼睛?”
泪意汹涌。这一刻他明白了,《拾痕录》从来不只是记录荣耀,更是打捞沉没的良知。有些人选择隐姓埋名,并非为了遗忘,而是为了让记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返回途中,他在额济纳旗汽车站偶然看见公告栏贴着一张旧照片展览海报,其中一幅标注为《胡杨林中的支教者》。他冲上前去,心脏几乎停跳??画面上那位裹着头巾、站在土坯教室前的女教师,眉骨轮廓、嘴角线条,分明就是孙亚男!
展牌说明写着:拍摄于1998年秋,作者为时任旗文化馆摄影干事李文秀之女??艾丽娅。
命运的丝线骤然收紧。
孟波当即拨通艾丽娅电话。这一次,她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孟老师,我知道她在哪儿。但我妈临终前交代,不到时机,不能说。现在……或许到了。”
原来,艾丽娅母亲李文秀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六十年代末有一位女战友曾在新疆短暂驻留,因肺部严重灼伤被迫退役。“她说话像打雷,笑起来能把房梁震下来。可说起死去的工友,一夜一夜哭。”两人约定,若有缘再见,便以一首歌为信物??苏联歌曲《喀秋莎》的第二段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