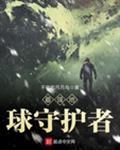笔趣阁>激荡1979! > 第504章 魏明的留学生活(第2页)
第504章 魏明的留学生活(第2页)
1997年,艾丽娅在一次边境医疗巡诊中遇到一位独居妇女,对方听见她哼唱《喀秋莎》,突然浑身颤抖,跪倒在地。从此两人建立秘密联系。近二十年间,艾丽娅定期送去药品和书籍,而那人则回赠手工缝制的棉鞋、绣着齿轮图案的枕套,以及一封封从未寄出的信。
“她不愿见外人,尤其记者。”艾丽娅说,“但她读过《拾痕录》,每本都翻烂了。上个月她托我带话:如果你们真的想写‘她们曾是少女’,那就写吧。只是别把我当英雄,我只求一件事??把我那年没来得及救下的三个姐妹的名字,印在书里。”
孟波握着手机,久久说不出话。窗外,夕阳正沉入戈壁,天地一片赤金。
一周后,他带着摄制组低调进入额济纳旗深处的一处废弃林场。远远望见一间土屋,烟囱冒着青烟。门前空地上,一位白发老人正在劈柴。她动作迟缓却不失力度,斧头起落间仍有当年抡钢钎的影子。
艾丽娅先行上前,轻轻哼起《喀秋莎》。老人猛然抬头,木柴落地。
镜头没有立即跟拍。导演懂分寸??有些相逢,必须先让灵魂喘息。
许久,孙亚男放下斧头,抹了把脸,走进屋内。片刻后,她捧出一只铁皮盒,交给孟波。盒子锈迹斑斑,锁扣已断,里面整齐码放着三十多本工作日志、数百张现场照片、一叠泛黄的请战书复印件,还有一枚早已失效的高温防护胸章。
日志扉页写着:
>“1976年4月12日夜班记录
>高炉突发煤气泄漏,班长命令撤离。我说不行,必须先关闭主阀。我和王桂芬、周小梅、刘素琴留下。
>最后一刻,我推她们进了安全通道。门关上了。
>我活了下来。她们没有。
>从此我不配叫自己的名字。我只是她们四个人的嘴,要替她们说出未说完的话;是她们四个人的眼,要看清这个世界的变与不变。”
孟波一页页翻看,手指微微发抖。那些血泪交织的夜晚、被掩盖的真相、层层上报却被压下的事故报告副本,如同一把把钝刀割开历史的结痂。而在1980年1月1日的日记中,她写道:
>“今天听说国家要搞改革开放。很好。但我更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牺牲,从来不算数?为什么纪念碑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媒体只写‘英雄集体’,却不肯写出任何一个女人的姓氏?
>如果这就是代价,那我宁愿继续沉默。”
当晚,众人围坐在土屋火塘边。孙亚男罕见地多说了几句:“那时候我们真傻啊。三十度的天气穿着棉袄上班,四十度的车间里穿着湿透的劳保服抢修。领导说‘轻伤不下火线’,我们就真敢拿身体堵漏气管道。可你知道最痛的是什么吗?不是烫伤,不是骨折,是事后没人记得你做过什么。”
她望着跳跃的火焰,眼神穿越时空:“有一次我晕倒在炉台边,醒来发现工友们轮流背着我走完十里夜路送医。路上谁都没说话,可每个人的汗味、喘息、脚步节奏,我都记了一辈子。那种情分,现在还有吗?”
没有人回答。只有火苗噼啪作响。
临别时,孙亚男交给孟波一封信,嘱咐必须在《拾痕录?第五辑》出版当天拆阅。除此之外,她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拍她的脸,不要用真实姓名,可以用化名“秦默”??取“沉默前行”之意。
回到北京,团队立即投入新一轮资料整理。技术部门将三百二十七页日志全部数字化,并通过AI语义分析提取关键词云:“责任”“姐妹”“炉火”“铭记”高频出现,而“荣誉”“表彰”几乎不见踪影。心理学专家据此撰写专题报告:创伤性记忆的选择性封存,往往源于社会认同缺失。
与此同时,关于“齿轮绕月”符号的研究也取得突破。经查证,该图案实为1970年代全国“三八女子炼钢班”联盟的秘密徽记,共涉及十八个省市五十六支队伍。目前确认仍在世的成员不足二十人,平均年龄八十二岁。她们散落在边疆小镇、矿区家属院、渔村陋巷,多数人终生未婚,无子女,如风中残烛。
孟波决定调整第五辑结构:不再按地域划分章节,而是以“青春切片”为主线,还原她们作为普通女孩的生命起点??
第一章《出发》,讲述她们如何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踏上未知征程。附录包括当年告别会上的演讲稿、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列车时刻表复印件;
第二章《淬火》,聚焦劳动现场的真实状态:高温、粉尘、性别歧视、生理期坚持上岗、生育后迅速返岗……配有原始考勤表、医务室就诊记录、内部通报文件;
第三章《断裂》,直面1976年后大规模裁员潮对女性工人的冲击。许多人因“不适合高强度作业”被劝退,无补偿,无安置,甚至被污名化为“情绪不稳定影响生产”;
第四章《余温》,记录她们此后的人生选择:有人改行当清洁工,有人回乡务农,有人终身守寡抚养烈士遗孤……但几乎所有人都保留着一块旧工作牌,或一枚褪色奖章。
最关键的第五章定名为《她们的名字》。整章仅做一件事:列出目前已知的五百三十七位“三八女子炼钢班”成员全名,并附简短生平。排版采用仿碑林格式,黑白肃穆,每一页底部标注:“本名录持续增补中”。
为此,项目组开通专项征集热线。短短半月,收到全国各地来电两千余次。一位山东老人颤巍巍送来妹妹的遗物:一双烧穿底的劳保鞋,鞋垫上绣着“争气”二字;浙江一位女儿翻出母亲箱底的搪瓷杯,内壁刻着“1973年度先进生产者??黄玉兰”;更有甚者,河南某村祠堂供桌上竟常年摆放着一位外嫁女的虚拟牌位,上书:“吾女秀珍,炼钢殉职,魂归故里。”
孟波亲自带队赴各地核实信息。在黑龙江双鸭山,他们见到八十七岁的张秀英。这位曾担任森林防火?望员的老人听力几近丧失,却坚持爬上三十米高的?望塔,指着远处山脊说:“那边,每年春天最先冒绿芽的地方,是我救过一场大火的阵地。”她掏出怀表,里面夹着一张合影??十五个姑娘穿着列宁装,笑容灿烂。如今,活着的只剩她一个。
“我们不是想当英雄。”她喃喃道,“我们只是不想输给时代。”
在湖北宜昌,长江航运公司仓库深处,发现了黄婉如保存完好的舵轮操作日志。这位九十二岁的女舵手至今每日步行五公里至江岸,望着货轮进出港。“我闭着眼都能画出这条水道的每一处暗礁。”她说,“可现在的孩子只知道导航仪,不知道水流会骗人,只有老船工的眼睛不会。”
最令人动容的是刘桂香的追忆。这位山西煤矿女工已于2001年病逝,家人交出她亲手绘制的井下巷道图,精确到每根支柱位置。其夫含泪讲述:她每次升井都浑身煤灰,却坚持洗三次澡才肯抱孩子。“她说井下死了太多姐妹,她不想把晦气带回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