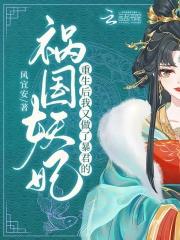笔趣阁>我爹是崇祯?那我只好造反了 > 第四百三十三章 内阁和六部怎么就成了叛徒(第2页)
第四百三十三章 内阁和六部怎么就成了叛徒(第2页)
台下掌声雷动,许多贫家父母泪流满面。
当晚,他在东宫书房写下一段话:“教育非为驯民,而为启智;非为巩固皇权,而为照亮黑暗。若有一日,十万寒门子弟能凭才学登堂入室,那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
然而,风暴总在最平静时酝酿。
六月初一,边关急奏:蒙古科尔沁部遭建州突袭,可汗重伤,部众溃散。多尔衮遣使至京,送来一封用满汉双语写就的国书,措辞倨傲:“明廷若愿割让辽东三卫、岁贡白银百万两,并送太子为人质,则两国罢兵言和;否则,明年开春,铁骑直捣燕京,鸡犬不留。”
满朝震动。
内阁首辅刘鸿训当场昏厥,礼部诸臣纷纷主张遣使议和,甚至有人提议“暂避南京,徐图恢复”。唯有朱慈?端坐不动,将国书投入炉中焚毁,冷声道:“建州蛮夷,不知礼仪,只懂刀剑。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刀剑。”
次日清晨,他登上正阳门城楼,擂响战鼓三百下。全国动员令正式发布:征召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丁壮入伍,凡参军者,家中免赋三年,本人授田五十亩;工匠优先录用为火器匠师,月俸加倍;阵亡者子女由国家抚养至成年,成绩优异者保送军校。
与此同时,他下令开启皇家武库,取出尘封多年的“神机营旧械图谱”,交由工部与民间巧匠共同改良。不到一月,新型“连环铳”问世??一次装填可连发五弹,射程达三百步,较传统鸟铳威力提升近倍。首批五百架试用于龙骧营,训练三日后即形成战斗力。
更令人振奋的是,山东即墨一位名叫赵三炮的铁匠,竟自行研制出“地雷阵触发机关”,能使数十枚铁壳地雷依序引爆,覆盖整片战场。朱慈?亲赴作坊查看,当场赐其“忠勇匠师”称号,授七品官衔,并拨款万两扩产。
七月十五,中元节。按例应祭祖赦囚,朱慈?却在这一天宣布:设立“军功爵制”。凡士兵斩敌一级,授“武勇士”称号,赏银五十两;斩十级者,擢为百夫长,赐田百亩;斩百级或擒敌将者,封县男,世袭禄米三百石。军官以此类推,唯不得世袭兵权。
诏书一出,举国热血沸腾。河南乡勇王五率三百庄丁北上投军,沿途高呼:“杀一个鞑子挣五十两!够娶十个媳妇!”山西猎户组团进京,自带弓弩猎具,愿编入斥候营。甚至连江南文人也掀起“投笔从戎”潮,翰林院庶吉士李渔写下《讨虏赋》,焚稿明志,奔赴前线。
八月初八,秋高气爽。朱慈?亲率三万新编“奋武军”出征,目标直指辽东。
临行前夜,他独自走入太庙,在崇祯灵位前静立良久。烛火摇曳中,他低声说道:“父皇,您一生勤勉,却总想以仁德感化天下。可这世道,光有仁德不够。儿臣知道,您最恨的是‘造反’二字。可若不掀翻这座腐朽的江山,如何救得了千千万万个赵二狗的母亲?如何对得起那些为你战死却不曾留下名字的将士?”
他跪下,重重叩首:“儿臣不孝,或将背负篡逆之名。但请容我一试??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大明的命脉。”
翌日黎明,大军开拔。旌旗蔽日,铠甲如雪。百姓夹道相送,老人递上热汤,孩童献上野花。一名盲眼老妪拄杖而来,颤巍巍递出一双布鞋:“听说太子爱穿粗布鞋,这是我孙女熬夜做的,愿您步步安稳,早破虏贼。”
朱慈?接过,郑重收入怀中。
行至卢沟桥,忽闻钟声悠扬。回头望去,忠魂碑前香火缭绕,无数纸钱随风飞舞,仿佛万千英灵护佑前行。
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吴三桂已率关宁铁骑出击,夺回宁远废墟;龙骧营第四镇奇袭敌后,焚毁粮草万余担;蒙古残部在新可汗率领下重返战场,切断建州退路。多尔衮被困山谷,屡次突围未成,伤亡惨重。
九月十九,决战打响。
朱慈?亲临前线指挥,以火器营为主力,布下“三叠阵”:前排地雷陷敌,中排连环铳齐射,后排骑兵包抄。建州八旗悍勇冲锋,然甫一踏入雷区,顿时血肉横飞。幸存者尚未稳住阵脚,五千连环铳同时击发,铅弹如暴雨倾泻。最后时刻,朱慈?亲自挥动令旗,关宁铁骑与奋武军骑兵两翼合围,彻底击溃敌军主力。
多尔衮身中三箭,乘乱逃遁,其所佩黄金虎符被缴获,随军亲王二人被俘,八旗牛录损失过半。
捷报传至京城,万民欢腾。百姓自发燃起篝火,孩童持灯笼游街,高唱新编童谣:“太子领兵破建州,鞑子哭着回老家。明年麦子堆满仓,还要给殿下磕个头!”
凯旋之日,朱慈?未入皇宫,而是径赴忠烈祠。他脱下战袍,换上素衣,捧着阵亡将士名录,逐一念诵姓名。每念一人,便点燃一支蜡烛。整整三天三夜,他未曾合眼,直到最后一支烛火点亮。
有人问他:“此战之后,可得太平?”
他站在祠前石阶上,望着远方青山,轻声道:“太平不会从天而降。今日我们打赢了一场仗,明日还会有新的敌人。但我相信,只要民心不倒,火种不灭,纵使千难万险,终有光明到来的一天。”
冬至那天,他在宫中设宴,邀百姓名流共饮。席间有老儒问道:“殿下如此为民,若有一天皇位更易,您当如何?”
朱慈?举杯微笑:“皇位不过是块牌匾。真正重要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能否吃饱饭、睡安稳觉、孩子有书读、老人有棺材。至于谁坐在龙椅上……只要他能做到这些,我便心满意足。”
话音落下,满座默然,继而掌声如雷。
窗外,雪花静静飘落,覆盖了旧宫墙的斑驳裂痕。而在京郊田野上,新犁的泥土正等待春耕,如同这片历经劫难的江山,悄然孕育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