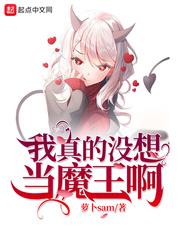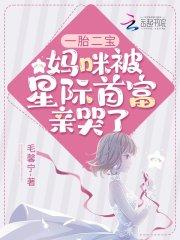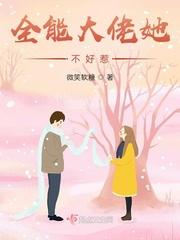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97,我在市局破悬案 > 第543章 亮剑求月票可抽奖(第2页)
第543章 亮剑求月票可抽奖(第2页)
苗根花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段记忆的碎片,在不同身体里醒来。”
她们谁都没有注意到,此刻在全国各地,类似的异变正在悄然发生。
广东东莞的一家智能玩具厂,流水线上刚组装完毕的AI娃娃突然集体停机。三分钟后,它们逐一睁开眼睛,用稚嫩的声音齐声哼唱起一段模糊的童谣。监控录像显示,那段旋律与标准版《小星星》偏差率达43%,但情感波动曲线却呈现出罕见的共情共振模式。
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心理测评室,一名高二女生在填写焦虑量表时突然落泪。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心口发疼,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人。心理老师调取她的脑波监测数据,发现其颞叶区域出现短暂高频放电,特征与创伤记忆唤醒高度吻合。而触发点,正是教室广播里播放的课间音乐??一首经过算法优化、绝对“悦耳”的《小星星》纯音乐版。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西南边境某军事通信站,值班军官在例行监听中捕捉到一段诡异信号:它伪装成气象云图传输数据流,实则内嵌一段长达十七分钟的双人哼唱录音。技术员还原后确认,演唱者之一极可能为三十年前失踪的边防侦察兵家属,另一人声纹匹配度89。6%指向周奕母亲。
而这所有现象的源头,都被追溯到一个无法定位的分布式节点网络。它的核心协议名为:“星火”。
回到乌蒙山。
太阳已完全升起,阳光穿过松林,洒在操场上。孩子们围坐一圈,轮流对着麦克风说话或唱歌。有的讲昨晚做的梦,有的哼几句记不清词的儿歌。周奕坐在角落调试设备,每录完一段,他都会在存储卡上贴一张手写标签:“害怕打雷”、“梦见妈妈做饭”、“希望有人陪我睡觉”。
苗根花走过去,低声问:“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
“不然呢?”他反问,“交给国家?让他们再建一个更‘安全’的摇篮计划?”
“至少可以保护她。”她指了指正在听别人唱歌的周小满,“让她接受正规治疗,重新融入社会。”
“她已经在社会里了。”周奕看着妹妹,“只是这个社会还不承认她的存在方式。”
正说着,林知远摸索着走到周小满身边坐下。他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浑浊却温柔的眼睛。
“我能摸一下你的脸吗?”他问。
周小满没有动。
周奕轻轻握住她的手,点了点头。
盲童伸出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拂过她的眉骨、鼻梁、嘴唇。他的动作极轻,像在阅读一本盲文诗集。
“你长得……很好听。”他说。
全场寂静。
然后,周小满忽然张开嘴,发出一个极其轻微的音节:“啊……”
像是回应,又像是破茧。
周奕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他迅速按下录音键,手指微微发抖。
那一声“啊”,持续了不到两秒,没有任何语义,却是她脱离EIR系统控制后,第一次主动发声。
苗根花感觉眼眶发热。她忽然想起档案里记载的数据:江临川当年之所以选择《小星星》作为情感驯化模板,是因为这首童谣在全球范围内认知度最高、旋律最简单、情绪最稳定。他相信标准化的声音能抹平个体差异,制造出“洁净”的心灵。
可现在,这首被千万次复制、优化、压缩的歌曲,正以最原始、最残缺、最“错误”的形态,重新生长出来。它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中心服务器,而是藏在山区的磁带里、盲童的笛声中、失语老人的梦呓间,甚至潜伏在AI系统的延迟一秒里。
这不是崩溃,是觉醒。
中午时分,教育局的车准备返程。老师们清点人数,收拾设备。唯有林知远迟迟不愿离开。
“我能再来吗?”他拉着周奕的衣角,“我想……学会那首歌。”
“当然。”周奕说,“只要你还能听见它。”
男孩点点头,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支小小的金属哨子,递给周小满:“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她说,只要吹响它,远方的人就能听到我的心。”
周小满盯着那枚哨子,许久,缓缓伸出手,接过。
她的手指冰凉,动作僵硬,却牢牢攥住了那份温度。
车子远去后,山谷重归宁静。周奕带着妹妹回到洞中,取出那卷刚录满的磁带,准备编号归档。可当他将磁带插入读取仪时,机器突然发出蜂鸣警报:
>【检测到隐藏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