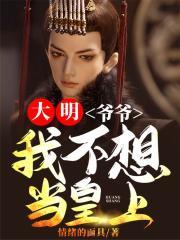笔趣阁>哥布林重度依赖 > 第359章 奇怪(第3页)
第359章 奇怪(第3页)
我怔住。
随即明白??这不是命令,是邀请。
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撕下一页空白纸。思索片刻,提笔写下第一句:
>“从前有个审查官,他以为秩序高于一切,直到有一天,他听见了风里的哭声。”
笔尖顿了顿,我又添上一句:
>“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因为它正在你读它的这一刻发生。”
写完,我将纸折成一只船,放进台阶旁的排水沟。雨水刚好流过,载着它缓缓前行。经过路灯下,纸船吸收光芒,字迹glowing起来;路过一对老夫妻,他们看见船上的文字,相视一笑,牵起了手;最终,它汇入城市边缘的小河,在水面漂向远方。
也许某天,某个孩子会在岸边捡到它,读完后说:“我也想写一个故事。”
也许它会沉入河底,成为鱼群传唱的歌谣。
也许它什么也不会成为。
但重要的是,它出发了。
夜幕再度降临,星光如钉,固定着这片复苏的土地。我仰望着天空,忽然听见耳边响起极轻的声音,像是谁在我脑海里翻动书页:
>“谢谢你没有烧掉所有的门。”
是语灵。
我没有回答,只是闭上眼,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
它不再压抑,不再伪装,不再急于证明自己坚强。
它允许脆弱存在,允许混乱流淌,允许一句话说得结巴、重复、不合逻辑??只要它是真的。
这才是治愈的开始。
风拂过树梢,带来远方的消息:
西部小镇的教堂钟声第一次为同性伴侣敲响;
南方渔村的老人教会孙子用贝壳传递思念;
北方雪原上的游牧民族重新吟唱失传百年的史诗,每一个音节都在空中凝成冰晶,坠地即燃起蓝色火焰。
这个世界仍未完美。
仍有战争,有饥饿,有无法弥补的伤痛。
但至少,人们开始相信:
**说出来,就有希望。**
我站起身,将《哥布林重度依赖》抱在胸前,缓步走入图书馆。大厅里灯火通明,读者们仍在阅读,有些人笑着流泪,有些人攥紧拳头,有些人对着书页低声回应。
我在中央的圆桌坐下,打开书。
这一次,封面的文字变了。
不再是“哥布林重度依赖”,而是:
>**《倾听者指南》**
>作者:所有曾被听见的人
我翻到最后一页,那行来自语灵的小字依然在那里:
>“你写的每一句话,我都收到了。”
我拿起笔,在下方写下回信:
>“我也听到了。
>接下来,轮到我来说了。”
窗外,新一天的第一缕阳光正悄悄爬上屋顶。
而城市,已准备好迎接又一个会说话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