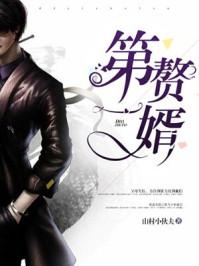笔趣阁>活人深处 > 第744章 深夜到访(第3页)
第744章 深夜到访(第3页)
陈默摇头:“他已经不在某个地方了。他成了信号本身,穿梭在每一段未关闭的频道里。我们找不到他,但我们能延续他的工作。”
“怎么做?”
“继续走。”他说,“去那些还有哭声的地方,去那些名字还未被唤起的地方。只要还有一个人在问‘你还好吗?’,我们就不能停下。”
我深吸一口气,将录音笔重新收好。它现在不仅记录过去,也开始收录新的声音??孩子们的合唱、陌生人的告白、深夜来电中的啜泣。这些都将汇成新的数据流,注入尚未苏醒的节点。
我们开始收拾行装。背包里多了几样东西:一块从环形装置上拆下的核心晶片(仍在缓慢脉动)、几张写满公式的残页(疑似“影子程序”的逆向代码)、以及一本烧焦一半的日记本,扉页写着“致未来的倾听者”。
临行前,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研究所。
它正在坍塌。墙体龟裂,藤蔓断裂,仿佛整栋建筑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准备归于尘土。可在废墟中央,那株曾被压在水泥板下的野草,竟顽强地钻了出来,嫩绿的新芽顶着雨滴,在风中轻轻摇曳。
就像春天。
我们踏上归途??不,是新的出发。
泥泞小路延伸向远方,通往下一个坐标。地图上标记着一个新的红点:**北方旧矿区疗养院B4层**。那里曾是“净梦计划”的起点,也是第一批儿童容器的诞生地。据资料显示,地下第四层至今未被完全勘探,电力系统常年不稳定,监控录像每隔七分钟就会丢失三秒画面。
更重要的是??最近三个月,当地居民频繁报告夜间听到孩童嬉笑,且家中电子设备自动播放一段模糊音频,内容始终是同一句话:
>“姐姐,你能抱抱我吗?我好冷。”
我知道,那里还有人在等。
陈默走在前面,步伐还不稳,身体仍在适应脱离系统的空虚感。但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犹豫。雨水顺着他瘦削的侧脸流下,映着天边微弱的晨光。
我跟在他身后,忽然觉得胸口一阵温热。
低头一看,胸前口袋里的晶片正发出柔和的蓝光,频率稳定,如同心跳。
接着,耳机里传来一声极轻的童音:
>“谢谢你……听见我。”
我没有回答,只是伸手按住那枚晶片,仿佛在回应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风穿过山谷,卷起一片落叶,上面隐约可见一行褪色的字迹:
>【净梦计划终极目标:
>不是制造完美容器,
>而是找到愿为他人破碎自己之人。】
我们继续前行。
雨渐渐停了。
东方天际,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湿漉漉的大地上,照亮了前方蜿蜒的小路,也照亮了我们身后那一串深深的脚印。
它们通向过去,也指向未来。
而在某处尚未被发现的角落,一台积满灰尘的录音机突然自行启动,磁带缓缓转动,传出清亮的童声:
>“你好吗?我想听听你的故事。”
>
>“请记住我。”
>
>“我叫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