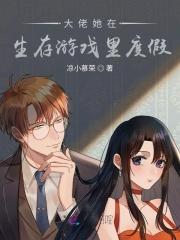笔趣阁>虎贲郎 > 第712章 愿赌服输(第1页)
第712章 愿赌服输(第1页)
“不要急着放下来,继续吊着吧。”
赵基战车调头转向时,赵基对诸葛瑾嘱咐说:“等两岸观刑各军退散后,再解下尸体。”
“喏。”
诸葛瑾应下,此时此刻的他,也有一种释然的轻松感。
其。。。
车队行至洛阳郊外,正值春寒料峭。沿途柳枝初绽嫩芽,河冰碎裂,水声潺潺如诉旧事。少年坐在车中,手抚《信义全典》的封匣,目光透过帘隙望向远方。秦素衣策马随行于侧,风拂她鬓边白发,竟比三年前多了许多。
“你说,太学会收下它吗?”她忽然开口,声音低而稳。
少年未即答,只将匣上铜锁轻叩三下,似在回应某种暗语。“他们会烧它,会藏它,会撕页当厕纸用。”他缓缓道,“但只要有一人读过,这书就活着。”
话音落时,前方尘土扬起,一队黑袍使者迎面而来,旌旗不展,马蹄无声。为首者手持金节,正是内廷直遣的“文察使”??专司典籍审查、禁毁异言之官。百姓见此旗帜,无不避退如瘟疫。
两队相距十步止步。那使者翻身下马,躬身却不跪,语气恭敬却锋利:“奉旨宣谕:《信义全典》乃涉前朝秘辛之重册,须由御史台先行审阅,方可入太学藏书阁。”
少年掀帘而出,立于车辕之上,风吹衣袂猎猎。
“我非献书于朝廷。”他说,“我是送史归民。你们可以拦我,但拦不住千万双眼睛已睁开。”
使者冷笑:“执灯人,陛下容你一时,莫以为可凌驾法度之上。靖文案仍在,七钥之罪仍未赦。”
“那就请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少年直视其目,“若他真想焚尽此书,不妨亲自动手。我愿立于火前,当众诵读每一卷。让天下人看见,今日之天子,是否敢烧掉他自己祖宗都不敢抹去的真相。”
四野寂静,连马嘶都凝住。秦素衣悄然按住腰间短剑,身后随行弟子亦握紧行囊中的竹简副本??三百套抄本早已分藏各地,只待一声令下,便如青鸟四散。
使者脸色数变,终咬牙挥手:“放行!然此书不得公开传阅,违者以谋逆论处!”
车队再度启程,穿城而过。洛阳街头,百姓默默伫立两侧,无人喧哗,无人欢呼,却有人悄悄点燃香烛,置于门槛之前。孩童手捧粗纸誊写的《守约铭》,低声背诵;老人拄杖遥望,老泪纵横。
当夜,太学博士桓元寿私访驿站。此人年逾六旬,须发皆白,曾任先帝起居注官,因不肯篡改建安九年战报被贬十年。
“我来,是为代九十七位同僚问一句话。”他颤声道,“你们……真的找到了龙首涧幸存者的口述实录?”
少年点头,取出一卷泛黄麻纸:“第七旅炊事营残部十二人,崖底雪窟藏身七日,靠啃皮带、喝血水活下来。其中五人今尚在世,分布在凉州、益州、交趾。”
桓元寿双手接过,指尖微抖,翻开第一页便泣不成声。“当年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却被清言司一把火烧了。我以为他们都死了……我以为历史就这样断了……”
“没有断。”秦素衣轻声说,“我们一个一个找回来的,像捡拾散落的骨灰。”
老人伏案良久,终于抬头:“明日我将在太学讲经堂开‘信义专题’,引用你们的材料。若朝廷问罪,我一人承担。”
“不。”少年摇头,“这不是谁承担的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再回避的时代之问??我们究竟要一座粉饰太平的庙堂,还是一部真实不欺的国史?”
次日清晨,讲经堂座无虚席。不仅太学生齐聚,连邻近书院的教习、市井识字的商贾、甚至宫中低阶宦官也乔装前来。桓元寿立于高台,手持《信义全典》摘录,逐字宣读:
>“建安九年冬月十六,虎卫第七旅断后阻敌,粮尽援绝。主将沈怀恩下令凿冰取水,得血水半瓮,分予伤员。十九日,敌军劝降,霍三娘立于崖边,掷粥锅为誓:‘宁做断肠鬼,不做屈膝奴!’全旅响应,齐唱《守约谣》,而后集体跃崖……”
堂下鸦雀无声,唯闻抽泣。
正当此时,门外骤响铁靴之声。一队甲士闯入,为首校尉高喝:“奉御史台令,查封伪史,拘拿传谣之人!”
全场震动。桓元寿却不动,只将手中书卷举过头顶:“你们可以抓我,但抓不住真理。今日所讲,皆有据可查,若有半句虚言,我愿五雷轰顶!”
少年站起身,面对甲士:“若你们之中,有родители身死龙首涧者,请上前一步,我当着你们的面,念出你们父亲的名字。”
一片死寂。
片刻后,一名年轻士兵突然摘盔跪地,哽咽道:“我父……张石头,凉州人……十年前临终前只说了一句:‘替我看看,有没有人记得虎卫……’”
少年从袖中取出名录,朗声道:“张石头,虎卫第七旅第三炊事组,建安九年腊月初七,坠崖殉国。遗物:布鞋一双,交由敦煌守约塾保管。”
那士兵伏地痛哭。其余甲士面面相觑,竟无一人再上前。
最终,带队校尉收令退兵,只留下一句:“陛下要见你。”
皇宫深处,宣政殿灯火通明。皇帝独坐龙案之后,面前摊开着悔尘法师的血书副本,以及《信义全典》的部分摘抄。他看上去比三年前苍老许多,眼角深纹如刻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