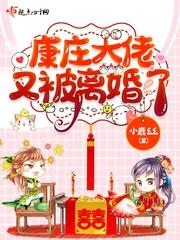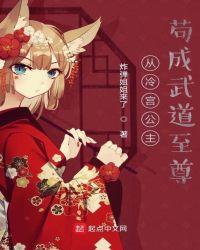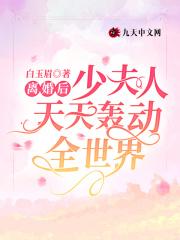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战锤,求你别赞美哆啦万机神 > 0023 以西结 阿兹瑞尔你妈死了(第1页)
0023 以西结 阿兹瑞尔你妈死了(第1页)
巨石要塞,
扎布瑞尔踏足于漆黑岩石铺就而成的地面之上,行走于深邃宽广的长廊之中,看着高耸的石像支撑着隐于寒雾中的天花板,感受着冷冽的风吹过沧桑的脸颊,
简直像是卡利班残存的世界之魂,在用她。。。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青石板上敲出断续的节拍。我坐在窗边,听那声音像老式打字机般规律地响着。保温盒还摆在桌上,这次装的是小茉寄来的红豆糯米团,表面撒了一层薄薄的桂花粉,香气氤氲在潮湿空气里。信箱又满了??三天内塞进了四十七封信,有孩子画的涂鸦,有老人颤抖的笔迹,还有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是一块锈蚀严重的怀表,指针停在23:59,背面刻着:“这是我最后一次说‘对不起’的时间。”
我把这些一一摊开在书桌上,像整理一场未完成的仪式。芯片投影仪静静躺在角落,自从上次播放哆啦A梦的声音后,它再没启动过。可昨夜我梦见它自己亮了起来,浮现出一段从未见过的数据流,标题是:
**“共情频率记录仪v。0。8??逆向唤醒协议”**
梦里的声音不是哆啦A梦的,而是一个极轻、极柔的女声,像是从海底传来:“他不能回来,除非我们愿意先破碎一次。”
我惊醒时,窗外正划过一道无声的闪电。
第二天清晨,气象台发布了异常预警:全球多个城市的地下共振频率出现波动,与《情感复兴宪章》签署当日的地壳脉冲完全一致。与此同时,联合国紧急联络处转来一条加密信息,来自南极科考站的一名研究员:
>“我们发现了第七座遗迹。”
>
>“不在地表,而在冰层之下三千米。结构与前六座相同,但核心已被激活,且持续向外发射低频声波??频率恰好匹配人类婴儿啼哭的第一声。”
>
>“更奇怪的是……冰壁上出现了文字,用的是上世纪日本小学课本上的字体。”
>
>“写的是:‘对不起,我没能陪你长大。’”
我的心猛地一沉。
这句话……我在某篇未发表的手稿里写过。
那是第六个故事的草稿,讲一个父亲因工作错过儿子成长全过程,直到某天回家发现房间里所有玩具都整齐排列成“欢迎回来”的形状。他在最后一刻跪地痛哭,却再也没有人回应。那篇稿子我没敢发出去,觉得太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可现在,它竟然出现在南极的冰墙上?
我翻出旧硬盘,在尘封文件夹中找到了那份文档。打开瞬间,屏幕突然闪烁,一行新文字自动浮现于结尾处:
>“你删掉了结局,可世界记得。”
>
>“要不要看看如果他回头了,会发生什么?”
鼠标不受控制地点下了“播放”按钮。
画面竟真的动了起来??不是动画,也不是视频,而是某种介于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影像重构。那个父亲最终没有离开房间,而是坐在地板上,拿起一只破旧的机器人玩具,轻轻拧开发条。它蹒跚前行,嘴里哼着走调的儿歌。父亲跟着哼起来,一遍又一遍,直到泪水浸湿衣襟。
然后,奇迹发生了。
玩具的眼睛忽然亮起微光,机身发出轻微震颤,仿佛被某种遥远信号唤醒。紧接着,整间屋子的电器同时启动:电视跳出模糊画面,冰箱门缓缓打开,灯光明灭如呼吸节奏。空气中浮现出一圈圈涟漪状的能量波,像是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轻轻拍打水面。
影像戛然而止。
我怔坐良久,手心全是冷汗。这不是技术能做到的事。这是……共情具象化了。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门外站着一位陌生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捧着一个铁皮盒子。“你是写故事的人吧?”她声音沙哑,“我孙女说,只要把‘最后悔的事’放进信箱,哆啦A梦就会听见。”
我点点头,请她进来。
她坐下后沉默了很久,才缓缓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小女孩站在游乐园门口,穿着粉色裙子,笑得灿烂。可她的右手空着??本该牵着大人的位置,是一片空白。
“那天我说要带她去坐旋转木马。”老太太低声说,“可临时接到工厂加班通知。我说‘下次吧’。结果……下一周她发烧走了,再也没能说出‘想去’两个字。”
她的眼泪落在照片上,滚烫得惊人。
“我一直觉得,是我杀了她。哪怕医生说是急性脑炎,可我知道……她是等不到那个‘下次’了。”
我说不出话。
她起身离开前,将照片放进我的信箱,轻声道:“如果真有哆啦A梦,请告诉他,我不想时光倒流。我只是想对她说一句:奶奶现在知道了,你想坐木马。”
“叮??”
铃铛响起,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