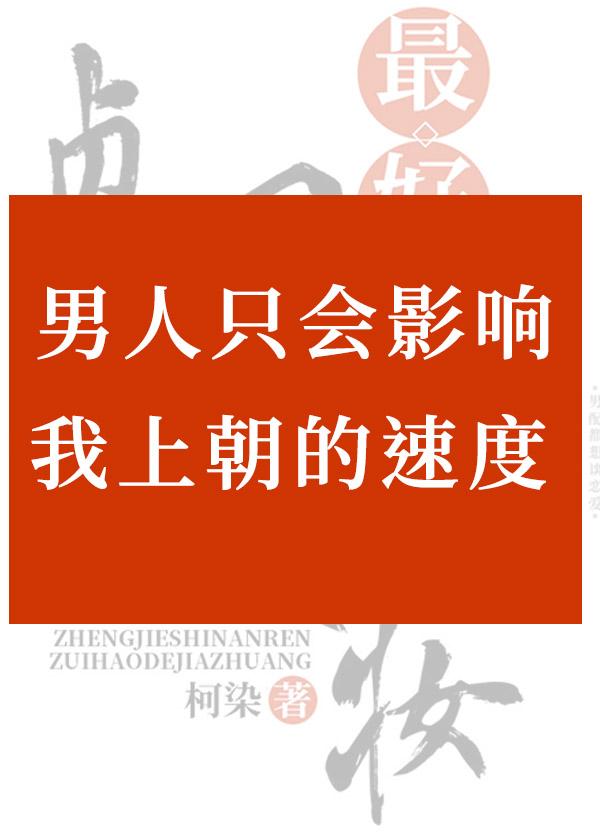笔趣阁>将北伐进行到底 > 第一百二十二章 今日边庭羽书至(第2页)
第一百二十二章 今日边庭羽书至(第2页)
刘淮解开水囊,猛灌了几口之后,方才叹了口气。
行军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想象,暑气与河流地形造成的影响远比庙算之中要大上许多。
昨日渡过黄河岔流时,饶是济州有半永久式的浮桥,却还是因为宽度问题而使得渡河缓慢,用了半日时间方才彻底渡过,却又因为天色已晚,不得不在黄河流南岸暂住一夜。
今日清晨行军之时,不知道是因为靠近河流的原因,还是这气温本身就不正常,暑气蒸腾得厉害,全军上下俱是恹恹。
刘淮在军中来回奔驰,查探士卒情况,心中再焦急,见状也只能下令暂时歇息一晚。
除了要维持军心士气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前方军情未明,说不得抵达战场之后就得立即投入战斗,刘淮也不可能将麾下精锐搞得精疲力竭,再被金军占个以逸待劳的便宜。
事实上,此时刘淮别说了解战场究竟是什么情况了,就连如今金军已经攻入徐州,还是依旧在啃宿州都不知道。
不过刘淮有个预感,随着距离中原越来越近,军情很快就能探查清楚了。
果真,就在傍晚暑气渐消之时,魏昌亲自带着一名军使走进了帅帐:“阿兄,刚刚咱们的游骑接应到了阿爹那边派来的军使。”
军使不知道是累得,还是因为松了一口气后浑身酸软,直接瘫坐于地,并从怀中掏出一个木匣:“都统郎君,元帅就在蕲县被金贼围攻,金贼来了一万五千众的精锐甲骑,还携带许多火药,我出发那一日,也就是七月初四,
金贼炸开了城门,却被我军堵住,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还望都统郎君速速来援。”
短短几句话让刘淮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般,听到蕲县城门已经被金贼炸开后,他几乎已经站了起来,却还是强忍着内心波动,捏住了手中木匣,作出一副大将之风的姿态。
“行,我知道了。”刘淮对着魏昌说道:“阿昌,你现在去寻一些吃食清水,让他就在此地吃饭歇息。”
魏昌走后,刘淮方才打开木匣,从其中取出数封书信,继续问道:“你是七月初四出发,今日七月初九,为何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到单州?”
军使立即说道:“不敢瞒都统郎君,我们几人分散向各地传讯,我去往河北走的是归德府,抵达曹州渡河之时,从知县处得知大郎君已经率军南下,我又折身回来追赶,方才耽搁了时间。”
刘淮一边缓缓点头,一边一目十行的看着书信。
其中言语十分详细,笔迹却是十分潦草,一看就知道是在仓促中写就的。
其中几封在写军情,倒也是一目了然,不过其余几封都是石据与魏胜的书信往来,其中还有魏胜的亲笔,在信中做出了判断,河南汉儿军似乎真的有投诚的意味。
刘淮看着魏胜的字迹,心中也有些无奈。
这个时代信息传递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宿州军情已经是五日之前的事情了。
而且石据既然有了投效之心,那就万万没有只跟魏胜交涉,却不派人来河北的道理。
说不定现在就已经有人拿着诚意抵达了大名府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谢九重在七月初八拿着石琚以及串联起来的汉儿军将领亲手花押的书信,抵达了大名府,想要当面以作投效。
何伯求又惊又喜,却不敢在此等大事上擅专,赶紧让军使带着屁股都快颠掉的谢九重来追刘淮,此时刚刚过了黄河。
但还是那句话,这年头消息传递速度实在是过于慢了,而事情又过于急迫了些,所以刘淮也就只能通过一半情报来脑补另一半的事实。
偏偏军情一日一变,需要他用最快的速度做出决断。
“阿昌,你怕死吗?”
刘淮对着重新回到营帐中的魏昌说道:“如今有项重任,我思来想去,竟然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
魏昌有些慌乱,他知道自家大兄不说大言,既然问他怕不怕死,那就是真的有极大生命危险。
不过作为数次上阵搏杀出来的悍将,魏昌还是咬牙说道:“还请大吩咐,我万死不辞。”
刘淮摊开一封札子,用炭笔在其上笔走龙蛇:“不用你万死,若是事事顺利,你说不得还会是此番中原大战最安全之人。”
“我要你带着我的文书,带着我的旗帜与令牌,充当我的诚意,去石据的河南汉儿军那里,将这两万兵马拉到我这一方来!”
魏昌没有阅读刚刚传递而来的军情,所以有些发懵:“石据。。。。。。那不是金贼的相公吗?如何就投靠我们了?”
刘淮摇头失笑:“谁知道呢?有可能是被排挤压得受不了了;也有可能是我在河北大胜,他作为一个河北士人有了选择;更有可能这厮就是个投机分子………………”
说到这里,刘淮手中炭笔微微停住,随后又叹道:“当然,若是按照梁军师所说,他这名师兄乃是有经天纬地之才,胸怀治国安邦之学,以安定汉地为己任。如今金国将汉地糟蹋成这副模样,石琚心中有所不平,倒也是寻
常。”
魏昌听得云山雾绕,却因为这是正经军令,终究不敢反驳,只是一时唯唯诺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