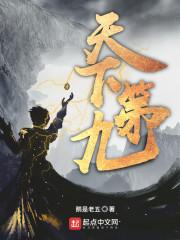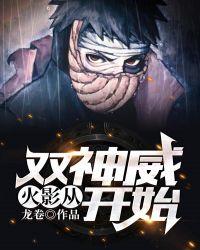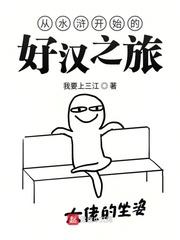笔趣阁>将北伐进行到底 > 第一百二十五章 明月照下趁夜袭下(第1页)
第一百二十五章 明月照下趁夜袭下(第1页)
萧仲达的做法堪称简单,甚至都有些粗暴。
在夜间之时,带领麾下兵马冲过去,直接在谯县周边鼓噪生事,或者干脆放一把火,将签军搞成乱军,从而在乱中夺城。
这并不是萧仲达拍脑门子决定的,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首先,作为金军中高层军官出身之人,萧仲达可太明白金国军事布置了。
在谯县这种远离前线的重要交通枢纽中,肯定会驻扎一些金国正军,然而却一定不会太多,最多也就是两百人,再加上军管之后从州县调度起来的土兵,就足以维持州县的安定了。
也就是说,如果想办法剥离州县地方兵马,只去对付金国正军,就很容易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
其次,萧仲达同样太明白签军是什么生存状态了,尤其是这么大规模的签军聚集在一起时,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巨大恐慌与骚动。
这是理所当然的,试想一下,一名青壮农夫在准备秋收之时,田产被掠夺,家人被驱赶或者杀害,而他则如同猪羊一般驱赶,整天处于饥渴难耐中,同时不断见到同行的签军死亡,到达某处之后,又被圈禁在旷野中,到底会
是个什么心情。
而如此多相似经历的人聚集在一起,根本就是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最后,萧仲达更是太明白他的好友萧曹乐了。
这厮是个榆木脑袋不假,却不是蠢货,相反十分聪明。
但一根筋的性子加上聪明的脑袋瓜,则会让他在仓促遭遇变故的时候变得极其多疑。
这也就给了萧仲达可乘之机。
月上中天,子时已到。
就在两百里之外,纥石烈良弼与夹谷清臣谈古论今,互相感慨之时,萧仲达手持长矛,沐浴在清冷的月光之下,看向了谯县城头。
彼处只有火把点点罢了。
“举火!儿郎们,鼓噪起来!”
牵着袍泽腰带艰难行军的二百余前锋兵马立即举火,吐出口中衔枚,贴近了签军大营:“谯县反!杀金贼!”
“造反了!杀金贼!”
在签军大营维持秩序的谯县土兵立即警醒,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有动作,就见到萧仲达带人破门而入,见到阻拦之人就杀,很快就将周边搞得一片混乱。
而在远方一片树林之后举火等待的朱长水见到这一幕,立即率领后续兵马快步追了上去。
萧仲达虽然已经蹉跎了两年,但一旦得以上阵,还是保持着顶尖武将本色,弓刀齐出,长兵乱砸,当者立毙,几乎没有一合之敌。
在乱战之中,一名顶尖武将的个人武力太重要了,在萧仲达连续以突袭的方式杀掉三名军官之后,签军营地彻底无救,发生了一种类似营啸般的躁动。
萧仲达见状,反而不敢继续掺和下去,将几段木栏推倒,给签军创造出逃跑通道之后,迅速收找麾下兵马撤了回去。
此时他带领的可不是神威军精锐,而是一群地方民兵与巡检兵混合在一起的杂牌军,若真的被签军揽进去,他可不觉得自己能将兵马收找回来。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签军营啸之后,迅速向着四面八方逃窜,连带着其余几处签军大营也不稳当起来。
就在此时,朱长水率领剩余的一千余人抵达,而到了之后,却没有立即作出进攻姿态,而是大声呼喊:“谯县反了!亳州反了!中原反了!中原汉儿杀鞑子!”
临涣距离此地不过二百里,口音是差不多的,在齐声呼喊之下,竟然真的有一种全城尽反的声势。
这下子就连那些依旧试图维持秩序的本地土兵也犹疑恐惧起来。
莫不是真的造反了吧?
怎么就没人事先通气呢?我连旗帜都没有准备啊!
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根筋而又十分聪慧的萧曹乐果真就陷入到了巨大的矛盾中,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一方面,以萧曹乐的坚持来说,他是真的想要为金国效忠的,而且他也相信自己的本事,这些时日足以拿捏谯县上下。
但另一方面则是,他又很确切的知道,中原汉儿经历了数年苦日子,今年终于要在石据主政之下而丰收一次,却又因为大规模征发签军而使得中原局势彻底大乱。
在这么一起一伏之下,中原汉人很有可能是真的要反的。
所以,在此等矛盾的心情之中,萧曹乐果断将麾下二百余正经兵马聚找起来,以防因为各自为战而被“谯县起义军”轻易绞杀,应对接下来的变局。
这个选择是无所谓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