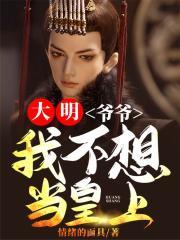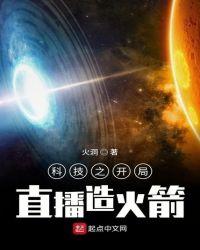笔趣阁>篡蒙:我岳父是成吉思汗 > 345章 大元恐怖无情的国力碾压懵逼的大理(第3页)
345章 大元恐怖无情的国力碾压懵逼的大理(第3页)
数月后,联合国正式将每年春分定为“双忆日”:上午纪念逝者,下午庆祝新生。这一天,忆堂开放所有私密记忆档案,允许公众自愿接入体验他人人生中最柔软的瞬间??一位母亲生产时的呻吟、一位老人临终前对孙儿的叮嘱、一名士兵在战场上为敌方伤员包扎的手势……
人们发现,越是敢于直面痛苦的记忆,越能激发出深切的温柔。
林念归并未出席仪式。他回到了敦煌,将老屋改建为一座小型忆馆,专收普通人捐赠的日常记忆碎片:一顿晚饭的笑声、一次雨中的散步、一封未寄出的情书……
某日黄昏,一个小女孩跑进馆内,递给他一片干枯的蒲公英茎秆,顶端还连着几缕残存的绒毛。
“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她说,“她说,这是从前你家门口飞出去的,她接住了一朵,养了好多年。”
林念归接过,指尖触到茎秆内部竟有一丝温热。他将其插入土盆,浇上青海湖运来的净水。
三天后,新芽破土而出,叶片呈罕见的金色,边缘泛着淡淡荧光。
植物学家赶来研究,惊呼发现其DNA中含有微量非地球源序列??与火星土壤样本中的远古孢子高度相似。
“它不该存在。”专家喃喃,“除非……记忆真的改变了物质。”
林念归只是静静看着那株幼苗,轻声道:“也许,有些东西从来就不该被分类、被解释。它们只是……该活着。”
那年冬天,全球气温骤降,极地冰盖加速融化,气候紊乱加剧。有人开始质疑:“既然痛苦不可避免,为何还要坚持共情?不如重启‘清醒者’计划,剔除脆弱的情感模块。”
响应者众。
关键时刻,那株金蒲公英突然开花。一夜之间,敦煌方圆百里所有的蒲公英同步绽放,绒球如星群腾空,随风北上,穿越国界,飘向北极圈。
卫星拍下惊人画面:当蒲公英云抵达废弃气象站上空时,原本持续发送“心蚀核”波形的信号塔突然静默,随后释放出一段全新广播??仍是婴儿啼哭,但这次,背景音里多了哼唱,是一首古老的摇篮曲,旋律跨越文化,几乎接近人类基因层面的安抚频率。
各国紧急会议召开,最终投票决定永久封存所有情感抑制技术,并签署《敦煌公约》:**任何试图系统性削弱人类共情能力的行为,视为反人类罪。**
签字当日,林念归独自登上鸣沙山。夜幕降临,繁星如织。他取出那本《林念归?未完成》,轻轻抛入风中。
书页未燃,却化作万千光点,升入银河,仿佛融入某颗遥远星辰的轨迹。
“我回来了。”他仰头低语,“你也看见了吗?”
无人应答。
但风中,似有一声极轻的回应,混在沙粒摩擦声里:
“嗯。”
多年后,新一代守忆者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段未标记的录音文件,录制时间正是林念归从“初忆之河”归来那天。音频内容仅有三秒,背景寂静,接着是一个男人极轻的叹息,然后是两个字,语气平静而释然:
“回家。”
文件命名为空白,但属性显示,创建地点位于火星轨道附近。
与此同时,在太阳系边缘,“归舟二号”探测器传回首张深空影像:画面中,那艘古老飞船仍在航行,舷窗内,外星孩童手中捧着的蒲公英早已凋零,但他仍每日为其浇水,嘴里反复练习着那个词。
而在飞船前方,宇宙尘埃自发排列成一条蜿蜒路径,宛如河流。
科学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唯有守忆者明白??
那是记忆本身,在星海中铺就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