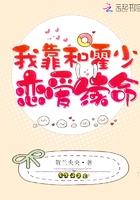笔趣阁>秦人的悠闲生活 > 第三百一十四章 早来的大雪(第3页)
第三百一十四章 早来的大雪(第3页)
混乱中,稂与谭露早已安排好退路。六十名少年分批撤离,有的混入观众,有的钻入地下渠道,更有十余人被接应船只载往渭水下游。
翌日,朝廷震怒。诏令全城戒严,搜捕“逆舞余党”,斩首示众者十二人,其余皆打入劳役营。
但奇怪的是,那六十名主角,竟无一人被捕。
而在民间,一首新谣悄然传开:
>“月娘娘,渡江来,
>sixty小儿唱悲哉。
>衣裂血色蓝,
>歌罢向天喊:
>楚虽三户,终亡秦??
>风起不在山,而在小儿唇!”
孩童们在街巷嬉戏时哼唱,妇人在织布时低吟,老兵在酒肆中痛饮高歌。
秦吏听之皱眉,却无法禁止??毕竟,只是童谣罢了。
寒冬降临,大雪覆城。
某夜,稂独坐灯下,整理近年所集文献。他将所有残卷、手抄、乐谱、童谣汇编成册,命名为《楚烬录》,共分五卷:
一曰《言》,收方言古字;
二曰《史》,录未删之楚事;
三曰《礼》,存祭祀仪轨;
四曰《乐》,载曲谱密语;
五曰《志》,记少年英名。
他知此书一旦落入秦手,必遭焚毁。于是命工匠打造三具空心铜鼎,将《楚烬录》分藏其内,一送往会稽兰舟村,一埋于彭泽旧祠地底,最后一具,竟沉入渭水深处,系以铁链锚于河床岩缝。
“只要有一本能留存,”他对谭露说,“百年之后,也会有人读到今天的故事。”
谭露点头,忽问:“你说,他们将来会怎么评价我们?”
稂望向窗外风雪,轻声道:“或许不会有任何记载。史书由胜利者书写,我们注定是‘叛逆’,是‘乱党’。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本就不为留名而战。”
“那为何而战?”
“为那些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稂说,“为那些尚未出生的灵魂。让他们有一天能站在阳光下,自由地说出‘我是楚人’,而不必恐惧。”
谭露沉默良久,终是展颜一笑:“那咱们还得继续种火。”
“当然。”稂提笔,在最新一页写下:
>**火种不灭,自有燎原之时。
>吾辈非为今日而活,乃为彼时而生。
>彼时若至,请唤我名。**
风雪渐歇,东方微白。
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接着是市集开铺的响动,车轮辘辘,人语依稀。新的一天开始了。
咸阳依旧巍峨,宫阙依旧森严。
但在某条小巷深处,一个五六岁的孩童正趴在窗台,跟着母亲轻声学唱: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声音稚嫩,却坚定。
如同春芽破土,无声,却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