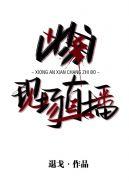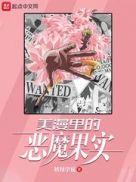笔趣阁>剑宗外门 > 第368章 杀意(第3页)
第368章 杀意(第3页)
“从今日起,我们将所有找回的抄本公开展示,不分来源,不论立场。允许公众自由比对、评议、质疑。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你看,就连‘真相’也会打架。但这没关系,重要的是??它们都敢出现。**”
决策定下,行动即启。
在记忆园东区,专门开辟“异文殿”,陈列所有不同版本的《万民书》。同一事件,可能有三到五个叙述版本,旁附考证说明、作者背景、成文时间。参观者可自行判断,也可提交反驳证据。
一位曾参与清言司的老吏前来参观,看到自己当年亲手焚毁的书稿竟完好存世,当场跪地痛哭。他写下忏悔书,详述自己如何奉命伪装成投书人,混入言城刺探情报,最终却被一篇关于饥荒中母亲易子而食的记述彻底击溃良心。
“我烧过十三车书。”他写道,“但我烧不掉那个画面。每晚闭眼,都是那双眼睛看着我,问我:你说过一句话吗?”
他的忏悔被录入《万民书?罪与醒卷》,编号04271。
与此同时,李承恩做出一个惊人决定:邀请当年推下父亲的宦官后代??一名年轻的礼部小吏,进入编纂组担任顾问。
“你不怕他报复?”有人担忧。
“我不怕。”李承恩答,“仇恨若代代相传,我们就永远走不出轮回。我要让他看看,他的祖先做了什么,也要让他明白,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
那名小吏起初抗拒,甚至怒斥李承恩“沽名钓誉”。但当他读完“西华门血录”全篇,尤其是看到自己曾祖父在日记中写道:“那一夜,我梦见被推下去的是我自己”时,他崩溃了。
三天后,他递交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家族史料整理报告,并申请永久加入《万民书》守护行列。
“我不是来赎罪的。”他说,“我是来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岁月流转,十年如梭。
贞元五十一年,记忆园迎来第十万个访客。那是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兵,双腿截肢,胸前挂着七枚勋章。他要求独自在照心碑前静坐一小时。
出来时,他泪流满面,却笑着。
“我终于敢看了。”他说,“以前总觉得对不起战友,因为他们死了,我活着。但现在我知道,只要我还记得他们,他们就没真正离开。”
同年冬,第一部由《万民书》改编的民间戏剧《碑语》在江南上演。全剧无台词,仅靠肢体、鼓乐与投影讲述三代守誓人的故事。最后一幕,演员们手持蜡烛,缓缓拼出“**勿忘**”二字,全场观众自发起身,齐声低诵《启智歌》。
而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开始模仿“忆馆”模式,建立“口传帐殿”,将部落史诗与受压迫经历代代传唱。有使者带来一封信,写道:“你们的笔,点燃了我们的火。”
李承恩已年过六旬,两鬓尽白,步履渐缓。但他每日仍坚持巡视园区,检查新收稿件,指导青年学子。
某日黄昏,他独自登上水晶碑顶,俯瞰整座记忆园。夕阳将万物染成金色,孩子们在回声廊嬉戏,老人在无名堂静静书写,情侣在照心碑前相拥许愿。
他摸出贴身收藏的那片枯叶。
叶片早已不再干瘪,反而在这些年吸收了无数誓言与泪水,变得柔韧光亮,脉络间隐隐泛出金纹。他轻轻一吹,叶片竟缓缓悬浮空中,随风飘向碑林深处,最终停在一棵新生的银杏树梢,宛如一枚永恒的书签。
他知道,祖父的遗愿完成了。
不只是《万民书》得以存续,更重要的是,**“记住”本身,已成为一种信仰**。
夜幕降临,第一颗星升起。
园区中央的铜钟被敲响,悠远绵长。
这一声,不是为控诉,不是为愤怒,而是为庆祝??庆祝人类终于学会,用记忆对抗遗忘,用真实战胜谎言。
李承恩站在风中,望着漫天星辰,轻声说道:
“父亲,娘亲,老师……你们听见了吗?
**我们,一直都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