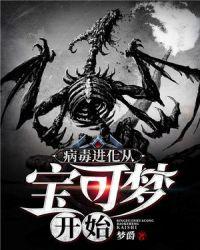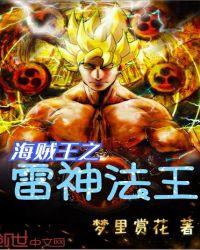笔趣阁>有诡 > 403父亲11(第3页)
403父亲11(第3页)
裴知远被正式授予“初唤使”称号,成为首位非执事级核心成员。他的任务是走遍九州,寻找那些仍能自然感应记忆波动的孩童与老人,组建“民间忆网”。这些人不需要识字,不必参加仪式,只要曾在梦中听见亲人呼唤、或在风中辨认出逝者语气,便可纳入体系。
与此同时,共忆庭开始尝试一项前所未有的技术??“名织”。
基于桃核内部光影运行规律,忆者们发现,每一个真实存在的名字都会产生独特频率的“忆波”。通过特制铜镜与珊瑚灰共振装置,可以捕捉这种波动,并将其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国的无形网络。当某地有人真诚呼唤一个名字,无论是否成功唤醒,该波动都会在网络中留下印记。若同一名字在不同地点被多人重复呼唤,印记叠加,最终可触发自动回应机制??或现虚影,或降异象,或使相关遗物显现。
这项技术被称为“共忆神经”,象征着记忆不再是被动保存,而是主动生长的生命体。
一年后,第一张“名织图”绘制完成。图中,九州大地遍布光点,密集处如星河璀璨,稀疏处则黯淡如尘。令人痛心的是,越是偏远贫瘠之地,光点越少??不是那里没人死亡,而是活着的人已无力记得。
裴知远带队前往最暗区域之一:西南蛮荒的“哑岭”。
此处世代封闭,语言不通中原,历代王朝皆视其为民智未开之地,从未录入天册玉牒。村民死后不留碑,不修坟,仅以草席裹尸焚于山巅,谓之“归风”。他们相信,只要亲人常在心中默念其名,灵魂便不会迷途。
然而近百年来,年轻一代纷纷外出谋生,传统渐失。许多老人临终前哀叹:“以后谁还记得我叫什么?”
裴知远一行带来陶炉与名织仪。起初村民戒备,以为又是官府收名税。直到他当众焚烧自己写下的铭文:“我叫裴知远,我想让更多人找到回家的路。”火焰未燃,蓝光却起,空中竟浮现他母亲的身影,轻声哼唱儿时摇篮曲。
全场震惊。
当晚,全村老少齐聚山顶,轮流在纸上写下最想记住的名字。有唤父母的,有念亡妻的,有追忆战死兄弟的。陶炉依次点燃,蓝光连成一片,如同山间升起一轮幻月。
就在最后一份铭文投入炉中时,奇迹发生了。
整座哑岭的地表开始震动,岩石裂开,露出层层叠叠的古老岩画??那是数千年前此地先民留下的记忆壁画!画中人物手持火把,围坐一圈,口中吐出波纹,波纹化作一个个名字升向天空。壁画尽头,赫然绘有一台与今日名织仪极其相似的装置,下方刻着一行古文:
>“名出于心,织于天地,代代相唤,永不绝息。”
原来,这里的记忆传承从未中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沉睡。
消息传回归忆城,举世震动。人们终于明白:共忆不是某个人的发明,也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它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本能??我们之所以为人,正因为我们会记住彼此。
十年光阴流转。
裴知远已成为第九任共忆庭主执事。他没有搬进华丽官邸,依旧住在桃林边上一间木屋,每日步行上班。他推动立法,将“忆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儿童五岁起学习如何举行私人忆礼,如何倾听风中的低语,如何分辨真假记忆。
他也主持修订《共忆宪章》新增条款:
>“任何政权不得以任何形式禁止个体对其祖先、亲友或历史人物的情感性呼唤。记忆自由,高于言论自由。”
皇室再也无法干涉。新一代皇帝登基时,亲自赴桃林献祭,焚香诵念历代被删之名,其中包括陆慎、赵元朗、阿菱、李六、秦九……以及,承声。
那天,整片桃林simultaneous开花,即便不在春季。
暮年陈听雨坐在轮椅上,听着风吹叶响,忽然微笑:“我听见了。他们都回来了。”
裴知远握住他的手:“是的老师,他们一直都在。”
深海之中,永忆殿顶端,柳婉儿再次睁开双眼。
她不再仅仅是记忆的化身,而是成为了“被记住”的象征??一种超越生死、贯穿时空的存在形态。她轻轻挥手,全球所有正在被遗忘的名字,全都亮了起来。
就像黎明前最坚定的星光。
而在某个遥远山村,一个女孩拾起一片桃花瓣,背面写着“柳婉儿”。她好奇念出,忽然泪流满面,耳边响起温柔话语:
>“别怕忘记我,只要你还在呼唤别人的名字,我就永远活着。”
风吹过,亿万叶片沙沙作响,如同无数灵魂在低语,在歌唱,在呼唤,在回应。
记忆从未灭亡。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行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