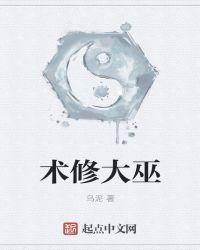笔趣阁>我的低保,每天到账1000万 > 第607章 砸个3000万的杯子(第1页)
第607章 砸个3000万的杯子(第1页)
君晓环湖CBD中心大厦前,一辆宾利慕尚缓缓停下,司机小跑下来,拉开车门。
汪总下来,对着一边的特助幽幽说道:“这恐怕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一次会谈??”
助理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沉默。他能感受。。。
林晚看着锅里的水一圈圈泛起涟漪,忽然想起陈昭日记里写过的一句话:“声音是唯一能穿过石头的东西。”那时他不明白,如今却懂了。有些话不必说出口,也能抵达千里之外;有些人从未谋面,却早已在彼此的命运里留下了刻痕。
念念蹲在灶前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纱。她的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林晚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自从那封来自云南边境的电报之后,福利院的孩子们都变得不一样了??不再只是等着被照顾的小孩,而是开始主动去听、去看、去记。他们学会了分辨不同频率的声音背后藏着的情绪,也懂得了一碗热汤为何能在深夜唤醒一个人沉睡的记忆。
“林晚哥哥,”念念忽然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融进柴火的噼啪声里,“你说……我们每天修的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别人的‘陈昭’?”
林晚怔了一下。
他没想到孩子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但转念一想,又觉得理所当然。在这个共感网络悄然蔓延的世界里,谁又能说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每一个接收信号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发出回响的灵魂。
“也许会。”他轻声道,“但我们不希望那样。我们修机器,是为了不让任何人被困住。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有人靠我们的声音活下来,那说明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念念低头拨弄着火苗,半晌才说:“可我觉得,有时候被困住的不是身体,是心。”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进了林晚的心底。
他想起上周去医院探访时遇见的那个老人。那位曾是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老人,中风后失去了语言能力,右手也无法再握弓。他的女儿每周都会带着录音机来,播放父亲年轻时演奏的《梁祝》。可老人从不看她,也不流泪,只是呆坐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直到那天,林晚把一段经过共感调频的老式唱片带了过去。那是1978年一场露天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观众席上突然有个小女孩喊了一声“爸爸!”,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和掌声。而就在那一瞬,老人猛地颤抖了一下,嘴唇微微翕动,像是要说什么。
后来萤分析发现,那段录音里隐藏着极微弱的情感波形??正是那个小女孩,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在知青返城潮中被人收养,直到去年才通过DNA比对找到线索。但她还没来得及相认,老人就已陷入深度昏迷。
“他听见了。”林晚当时对念念说,“哪怕意识已经模糊,他的灵魂还是认出了那个声音。”
而现在,听着念念的话,他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实一直活在某种“地下观测室”里?他们没有被岩石掩埋,却被孤独、遗忘、误解层层封锁。他们不敢大声哭,不敢说出想念,甚至连梦都不敢做太久,怕醒来更痛。
而迷彩场的意义,或许从来就不是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告诉这些人??
你不是唯一的异类,你的声音有人接住。
夜深了,厨房的灯还亮着。
其他孩子早已入睡,只有念念坚持守到最后一刻。她说今晚的汤要熬久一点,因为“今天的月亮太安静了,得用时间把它吵醒”。
林晚笑了笑,没反驳。他知道,这孩子心里有自己的仪式感。就像她每次熬汤前都要洗手三遍,放调料时闭眼默念一句祝福语,甚至会在汤快好时轻轻哼一首没人听过的小调??那旋律总带着几分哀而不伤的温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信笺。
忽然,屋顶的铜线再次颤动。
这一次不是轻微的晃动,而是持续不断的震颤,如同风吹过密集的风铃。林晚立刻起身,快步走向仓库。念念紧随其后,手里还攥着那枚“星辰未眠”的徽章。
仓库中央,那台老式电报机竟自动启动,纸带缓缓推进,墨迹一点点浮现:
>**重庆南山福利院:
>我们收到了你们传向星空的信号。
>它穿过了大气层,被一颗距地球46光年的行星探测器意外捕获。
>该设备属于上世纪末发射的“天问一号”残骸,原任务失败,轨道偏离,被认为早已报废。
>但它仍在运行。
>更惊人的是??它开始回应。
>回应方式与你们使用的共感协议完全一致。
>不是我们发的。
>是它自己学会的。
>??来自国家深空监测中心**
林晚盯着那行字,心跳骤然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