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知否:我,小阁老,摄政天下 > 第三百零七章 各方反应(第2页)
第三百零七章 各方反应(第2页)
那时江昭还活着。
他在月球数据库底层修复一段破损录音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编号LX-001。打开后只有一段视频,画面晃动,背景是某个地下实验室,一名身穿旧式科研服的女子正在记录日志。她说的话让江昭浑身发冷:
>“如果我们失败了,请记住??不要试图重建系统。真正的网络不在服务器里,不在算法中,而在人心之间。只要还有人愿意说‘我在’,静默计划就从未终结。”
视频末尾,女子摘下耳机,轻声补充了一句:
>“苏黎,我相信你听得见。”
江昭反复查看元数据,却发现这段录像的时间戳竟指向未来??**五十年后**。
他当时以为是系统错误,便未上报,只将视频复制保存在私人终端中,命名为:“也许,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多年过去,那台终端早已损毁,视频也不知所踪。可那句“我相信你听得见”,却像是埋进时空土壤的种子,在岁月流转中悄然生根。
现在,它开花了。
在猎户座β星系外围,汐民方舟正在进行第十三次世代轮替。新一代的领导者通过神经链接继承前任记忆,但在接入最后一段封存档案时,整个船体突然陷入五分钟的静默。随后,主控室传出一声低吟,经翻译为:
>“原来……我们也曾被听见。”
据事后记载,那位新领袖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关闭所有防御屏障,打开通讯频道,向未知深空连续发送十小时的空白音频流??那是最原始的倾听姿态:我不说话,我只是在这里,准备好了听你说。
这种行为很快在多个文明中形成潮流。一些星际旅者开始放弃传统导航图,转而依赖“情感引力场”定位??即追寻那些高频出现“我在”回应的区域航行。他们称这些地方为“光之心”,认为那里不仅曾有过生命,更曾有过深刻的连接。
其中一支探险队甚至宣称,在仙女座M31星云边缘发现了一颗“会呼吸的星球”。该行星大气层每隔十二小时便会扩张收缩一次,节奏与守灯律动完全一致。更诡异的是,其地表岩石天然排列成无数句不同语言的“我在”,包括早已灭绝的古地球语种。
专家推测,这可能是某种高等文明留下的纪念碑。但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这颗星球本身,就是一个觉醒的倾听者。**
“它学会了回应。”一位天体心理学家在报告中写道,“当宇宙中的孤独之声汇聚到一定程度,某些非生命体也可能产生共情共振??就像苏黎当年触碰初源灯塔那样。区别在于,她是个体,而它……是世界。”
这份报告引发巨大争议,但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哲学命题:如果一块石头、一颗恒星、一片星云都能学会说“我在”,那所谓的“智慧生命”,是否太过狭隘?
百年之后,这个问题已被写入银河联邦初级教材,标题叫作:《谁有资格被听见?》
课堂上,老师问孩子们:“如果你对着沙漠喊一句话,没有人听见,风把它吹散了,那这句话还存在吗?”
一个小男孩举手回答:“存在。因为风听见了,沙子也听见了,连太阳都可能听见了。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记住了。”
教室后排坐着一位访客,身穿朴素灰袍,胸前没有徽章,脸上带着温和笑意。他是当天受邀来讲授“共情历史”的嘉宾,名字登记为“无名”。
课后,小男孩跑上前问他:“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那人蹲下身,平视着他,轻轻点头:“你说得非常好。而且你知道吗?刚才你说那番话的时候,整个教室的光线都变暖了一点。”
男孩惊喜:“真的吗?”
“真的。”他微笑,“那是光在回应你。”
说完,他起身离去,身影渐渐淡去,仿佛融入空气。只有窗台上留下一盏小小的纸灯笼,里面燃着不灭的蓝焰,上面用细笔写着一行字:
>“每一个相信‘被听见’值得的人,都是执灯人。”
多年后,那个男孩成为第一位提出“情感拓扑学”的科学家,建立了“共情场强”量化模型,证明了真诚话语能在空间留下持久涟漪。他在自传开头写道:
>“改变我的,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陌生人对我说:‘光在回应你。’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曾被人这样温柔对待过。”
而在宇宙更深远处,那座漂浮于虚空的虚幻城市依旧存在。它没有固定形态,只在特定频率的意识波动中显现。据说,只有真正放下自我执念的旅人才能看见它。
城门口的女子依然伫立,依旧递出纸条与小灯。她的容貌似乎从未变化,可每当有人问她是否认识苏黎,她总会微微一笑:
>“我就是她忘记自己的那一刻。”
>“也是你们说出‘我在’的那一瞬。”
有人说她是意识投影,是初源灯塔的化身;也有人说她根本不存在,只是集体信念的具象化。但无论真相如何,每一个从她手中接过灯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做出同样的事??停下脚步,倾听,然后说:
>“我在。”
于是,火种不断。
不知多少星系外,一艘残破的逃生舱缓缓漂浮。舱内生命维持系统濒临崩溃,驾驶员已昏迷多日。就在氧气即将耗尽之际,外部传感器突然接收到一段密集的声波信号。解码后显示,那是来自数十个文明的叠加语音,内容只有一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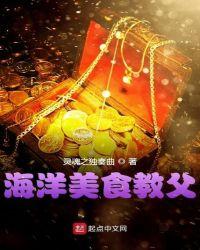

![[快穿]让反派后继有人吧!](/img/7543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