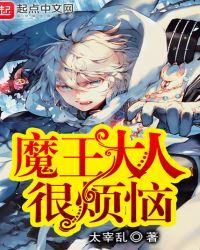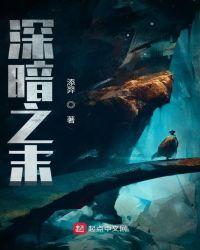笔趣阁>我才是徒弟们的随身老爷爷? > 第二百五十三章(第2页)
第二百五十三章(第2页)
“不错。”她抬手一引,空中浮现一幅巨大图景:一座由无数细线交织而成的网络,贯穿山河大地。每一条线,都连接着两个名字??施恩者与受助者;每一个节点,都闪烁着微弱蓝光。
“这叫‘仁网’。”她说,“它无形无相,却真实存在。十年来,你们誊写的每一本书、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加固这张网。如今,它已触及千万人心,哪怕皇帝下令斩断一万根绳索,也割不断最后一根??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相信。”
杨石头怔然良久,忽然问道:“那你呢?你为何一直在这里?你不曾飞升,也不成神,却守着这份执念千年不散?”
柳七娘笑容渐淡,眼中掠过一丝悲悯:“因为我忘不了。我忘不了战乱中那个把最后一口粮给我孩子的母亲,忘不了雪夜里为我遮风的老兵,忘不了临终前仍叮嘱学生‘继续写下去’的先生……我若闭眼,谁替他们记住?”
她顿了顿,轻声道:“所以我不走。我不是神明,也不是导师。我只是……不肯忘记的人之一。”
杨石头忽然跪下,深深叩首。
“我不求你庇佑。”他说,“只求继承你的不愿遗忘。”
柳七娘伸手虚扶,泪光闪动:“起来吧。你已不必拜我。因为你已是新的‘不肯闭眼者’。”
翌日清晨,杨石头启程南下。临行前,全村百姓齐聚村口相送。杨母拄拐立于槐树之下,颤声叮嘱:“儿啊,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回家的路。”
“娘,”他回头一笑,“我的心早就铺在这条路上了。”
他一路行至秦岭深处,沿途所见,皆是异象初显。某日路过小镇,见集市冷清,人人面色惶恐。打听才知,数日前有位游方讲习师在此宣讲《仁行录》,次日便暴毙街头,脖颈青紫,状似中毒。官府以“妖言惑众”定罪,焚其书稿,驱逐听众。
可就在杨石头抵达当晚,镇东破庙中忽闻歌声响起。他循声而去,只见十余孩童围坐残烛前,低声哼唱那三音旋律。墙上用炭笔写着几行歪斜字句:
>“昨日阿姐教我们唱一首歌,说听了就不怕黑。
>今晨听说阿姐死了,可她的声音还在。
>我们要把这首歌传出去,让她活在别人嘴里。”
杨石头站在门外,久久未语。直至歌声结束,他才推门而入,从竹篓中取出一本手抄册,递给最年长的女孩。
“这是新版的《仁行录》。”他说,“加了一章,叫‘殉道者名录’。她们的名字,一个都不能少。”
女孩接过,郑重捧在胸前,如同接过圣物。
此后月余,杨石头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他在驿站为旅人讲一段故事,在茶棚为商贾唱一曲短调,在田埂为农夫读一封孤儿家书。每到一处,便有人默默抄录,悄悄传播。有些地方官差闻讯追捕,却发现民众早已结成“耳语链”??一人传一句,十人汇一篇,百人共护一书。
更有奇者,某夜宿于荒村古宅,半夜惊醒,见满屋飘浮着淡淡蓝点,如萤火般环绕床榻。细看之下,竟是尘埃自发凝聚,映出一幕幕过往影像:一对夫妻冒死收留逃难书生,三日后双双被杀;一位女医无偿救治瘟疫村民,死后坟前无碑;一名少年为救落水同伴溺亡,家人反被讹诈……
“万民忆尘……”他喃喃道,“它们跟着我走了。”
他终于明白,这本书的力量,从来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人心之间的传递。每一次诵读,都是一次唤醒;每一次铭记,都是一次抵抗。
当他进入江南时,春雨绵绵。某日在桥头遇见那位盲眼老琴师,果然每日弹奏残调。路人笑其痴,杨石头却驻足聆听,竟从中辨出《护心曲》变奏??左手按弦模拟“do”,右手轮指打出“re-mi”,虽不成调,却精准契合频率。
他上前躬身行礼:“前辈可是曾在双护堂学艺?”
老琴师停下动作,浑浊双眼望向虚空:“你是……杨石头?”
“您认得我?”
“我认得这股气息。”他枯瘦手指轻抚琴身,“十年前,柳七娘最后一次公开讲习,就是用这把琴弹起序曲。后来琴毁人亡,我以为再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了……可这些年,我总觉得有人在远处回应我。原来是你。”
杨石头眼眶发热:“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
“你从未孤单。”老琴师微笑,“每一个还在坚持的人,都是你的战友。我们不会飞剑斩龙,也不会腾云驾雾,但我们守住了一样更重要的东西??**人性的回音**。”
那一夜,两人共坐桥头,一个弹,一个唱。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心中火焰。至凌晨时分,整座桥面竟泛起幽蓝微光,桥下河水倒映出万千人影,皆是历代言说善行者,静静伫立,仿佛列队致敬。
而在千里之外的长安皇宫,太子正独自批阅奏章。忽然,窗外飘来一阵童谣声。他侧耳倾听,竟是宫女们在教小皇子们吟唱新版《仁行录》改编曲。歌词朴素:
>“给饿的人饭吃,
>给冷的人衣穿,
>给哭的人抱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