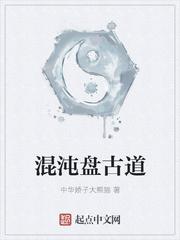笔趣阁>给,主说这个好使 > 81 拜恶魔(第2页)
81 拜恶魔(第2页)
叶知秋望着天空,忽然感到一阵眩晕。她扶住长椅,发现自己的手掌竟开始半透明化,血管中流动的不再是血液,而是一缕缕细微的银光。
“我也……被选中了?”她颤抖着问。
女孩转头看她:“你一直是。只是你一直以为自己只是见证者。”
“可我已经老了……”
“年龄不是界限,执念才是。”女孩走近她,“你还在等小舟回来,对吗?你以为只要守在这里,就能延续他的意志。但你知道他最后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吗?”
叶知秋怔住。
>“他说:‘别替我活着。去成为你自己未曾敢成为的样子。’”
泪水无声滑落。多年来,她整理笔记、培训共感师、主持仪式,一切行动都打着“为了小舟”的旗号。她以为这是忠诚,实则是逃避??逃避面对自己内心的空洞:那个从小被母亲遗弃、靠捡拾他人情绪维生的女孩,从未真正学会如何爱自己。
她蹲下身,将额头贴在银脉植物的根部。
“我害怕……”她哽咽,“如果我不再是他故事的一部分,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大地回应般轻轻震颤。花苞再度发光,这一次,投射出一幅影像:年轻的她站在医院走廊,手里攥着母亲临终前写的信,却没有勇气拆开;多年后,她在共感仪式上听到一个少女讲述相似经历,当场崩溃大哭??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借别人的痛疗愈自己”。
而现在,轮到她亲身经历了。
三天后,叶知秋宣布关闭“灰雾森林共感中心”的日常运营,只保留每月一次的开放日。她独自打包行李,带上那本破旧笔记本和一枚备用种子,登上了前往西伯利亚冻原的列车。
同行的只有两名志愿者,一名聋哑画家,一名退役战地记者。他们都不说话,但在共感训练中建立了深厚的默契。列车穿越雪原时,三人围坐一隅,用指尖在玻璃上写字交流。
>聋哑画家写道:“我画了二十年战争,却从没画过和平。我想试试。”
>战地记者写道:“我拍下了thousandsofdeaths,但没人记得名字。我想记录活下来的人怎么呼吸。”
>叶知秋写下最后一句:“我想找到那个把我母亲带走的雪夜,问问风,她有没有后悔。”
他们在北极圈内一个废弃气象站安营扎寨。这里曾是冷战时期的监听哨所,如今只剩锈蚀的天线塔和结冰的地下室。当地人称此地为“沉默之地”,据说每逢极夜,能听见地底传来孩童笑声。
第七个夜晚,暴风雪来袭。电力中断,通讯瘫痪。三人蜷缩在炉火旁,共享一条毯子。就在午夜钟声(他们自带的老式闹钟)响起时,地面突然裂开一道缝隙,幽蓝光芒从中溢出。
那是一株微型银脉植物,仅三十厘米高,却已结出一朵闭合的花苞。它生长的位置,正是当年气象站最后一次接收到神秘信号的坐标点。
叶知秋跪在地上,伸手触碰花瓣。瞬间,大量记忆涌入脑海:
??1978年冬,一名苏联女科学家在此研究极光异常,发现某种声波能在冰雪中传递情感。她试图建立“情感雷达”,却被上级视为异端。临终前,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刻在金属板上,埋入地下,并录下一段话:“也许未来会有人懂,爱也是一种物理现象。”
??她的女儿,五岁时被送往南方亲戚家,从此再未相见。而那位女儿,正是叶知秋的母亲。
火焰骤然变亮,映照出墙上斑驳的涂鸦。叶知秋凑近一看,竟是用俄文写的一句话:
**“亲爱的,如果你能听见,请告诉我你还好吗?”**
她捂住嘴,泪如雨下。
那一夜,她第一次主动释放了自己的全部记忆:童年的寒冷、被寄养的屈辱、对母亲的怨恨、对小舟的依恋、对自己软弱的羞耻……她不再压抑,不再解释,只是让它们如河水般自然流淌。
当最后一丝情绪释放完毕,花苞缓缓开启,从中飘出一张薄如蝉翼的金属片,上面密布着细小刻痕??正是那位女科学家留下的完整数据。
第二天清晨,阳光刺破云层。远处雪地上,十几名当地原住民儿童围成一圈,手中拿着叶知秋昨日教他们制作的“声音捕获器”(简易共鸣盒)。其中一个男孩突然喊道:“听!它在唱歌!”
众人静默。风掠过天线塔,发出奇异的颤音,仿佛整座废墟正在苏醒。那声音起初微弱,渐渐清晰,竟是一首古老的涅涅茨族摇篮曲,与叶知秋母亲常哼的调子惊人相似。
她取出随身携带的种子,轻轻埋入植物旁的冻土中。
“新的站点,不需要名字。”她说,“只需要一颗愿意倾听的心。”
与此同时,太平洋深处,林晚所在的裂谷区域再次传出音频。这次不再是童声合唱,而是一个清晰的提问:
>“我们还能继续做梦吗?只要还有人在听?”
全球共感网络自动转发这条信息,附带一行系统生成的文字:
**“你的回答,将决定下一粒种子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