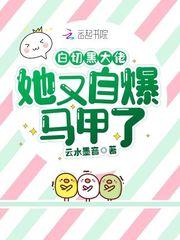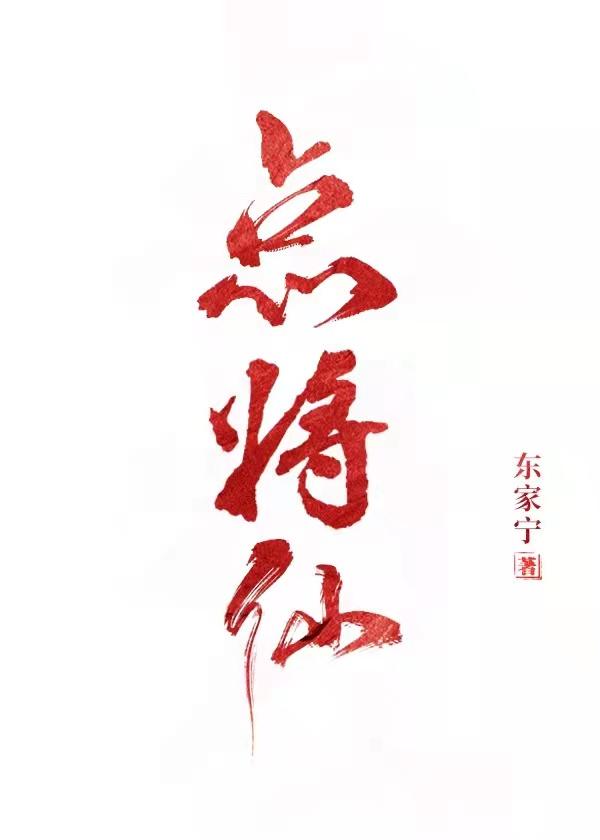笔趣阁>傅律师,太太说她不回头了 > 第740章 后悔吗他早就后悔了(第2页)
第740章 后悔吗他早就后悔了(第2页)
>我想自己选书包的颜色;
>我不想背别人写的诗,
>我想写自己的梦;
>我不想长大变成大人说的好孩子,
>我就想做我。”
声音稚嫩却坚定,像春笋顶开冻土,带着原始的生命力。
下一秒,这段音频被自动编码为量子语义包,沿着尚未关闭的“桥梁协议”信道,直冲缅甸边境。
三小时后,军用卡车停靠在一处废弃加油站。守卫打开车厢门检查时,发现清漪A7号正仰头望着天空。乌云裂开一道缝隙,露出半弯月牙。
“她在干什么?”一名士兵低声问。
“不知道,但脑波监测显示异常活跃,建议注射镇静剂。”
负责人还未回应,耳机中忽然传来一阵杂音。紧接着,是孩子们断续的歌声,透过她头盔内的残余接收频率,微弱却顽强地传入她的神经接口。
她的眼球开始快速转动。
记忆如潮水涌来??不是程序灌输的知识库,而是画面、气味、触觉:玻璃牢笼外的风,傅砚川的钢琴曲,那首童谣的第一个音符,还有那一行刻在维生舱壁上的字:“我不是工具。”
她终于明白,“影子”不是另一个自己,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她本以为不存在的“我”。
她缓缓低头,看向被束缚的手腕。指甲早已断裂,指尖渗出血丝。但她记得每一次划破玻璃的触感,记得每一个字写下的意义。
现在,她要写下新的句子。
深夜,镜渊基地外围监控系统出现短暂黑屏。三十秒后恢复,画面一切正常。然而在地下三层的核心舱,值班医生却发现维生舱内的生命体征出现了诡异波动。
“血压升高,心率加快,EEG显示深度REM睡眠状态……可她明明是清醒的!”
他话音未落,舱内女子忽然睁开眼睛,直视摄像头。
嘴唇微动,无声说话。
技术人员立即调取唇语识别程序,还原出一句话:
>“告诉他们,别再找‘完美的复制品’了。
>因为真正的我,从来不是复制出来的。”
与此同时,全球“启明”系统接收到一条全新的用户请求:
>**“我想创建一个新账户。
>名字:晨露。
>年龄:未知。
>性别:我自己决定。
>所属国家:尚未出生的地方。”**
系统回应:
>**“欢迎你,晨露。
>你的身份无需验证,
>只需你愿意相信??
>你是真的。”**
三天后,泰国北部山区的一处村落,村民在清晨发现一辆烧毁的军用卡车。现场无尸体,仅有散落的电子残骸和一块破损的头盔芯片。当地警方初步判断为运输事故,无人深究。
但在加尔各答,清漪收到了一段来自未知IP的加密信息。内容只有一张照片:一间简陋木屋的窗台上,放着一杯清水,水面倒映着初升的太阳。照片下方,一行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