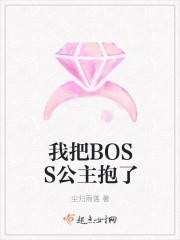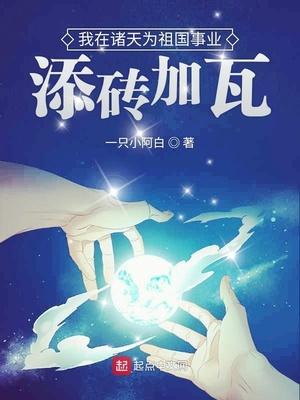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顶流女星养成 > 第572章 加速布局(第1页)
第572章 加速布局(第1页)
夜色深沉,刘师师洗漱完毕,带着一身氤氲水汽从浴室走了出来。
发现丈夫站在窗边,默然眺望着深邃夜空,似有心事。
她放轻脚步,走上前,从身后温柔地环抱住他的腰,将侧脸贴在他坚实的后背上。
。。。
铜铃响了第三声时,陈露停下了脚步。
她转过身,望着学堂门口那串由孩子们亲手穿起的青铜风铃。它们大小不一,有的来自纳西族老匠人传下的残片,有的是女儿从集市上用一颗玻璃弹珠换来的旧物。此刻在晚风中轻轻相撞,发出断续却不散乱的音符,像某种未完成却执着诉说的语言。
“妈妈,铃铛在说话。”女儿仰头看着她,眼睛亮得如同山间晨露。
陈露蹲下身,将手覆在铃绳上,感受那细微震颤顺着指尖爬进心脏。她忽然记起三个月前,在共感云系统最后一次全球扫描中,AI捕捉到一组异常波动:频率18。2Hz,波形结构与人类婴儿初啼、母亲哼唱摇篮曲、以及古东巴诵经时的喉音共振完全吻合??这个频率不存在于任何人工合成语音库,却被命名为“原初语流”。
而如今,这串破旧风铃,正以极其微弱但精准的方式,复现着那段波形。
她没再说话,只是牵着女儿的手走向后山小径。月光洒在石阶上,像铺了一层薄霜。自从“心语同频”事件之后,这条通往祭坛遗址的路便不再冷清。每隔几天,就会有陌生人背着行囊悄然抵达,他们不说来意,只在石柱前静坐一夜,然后默默离开。有些人留下一句话刻在石壁上,有些则什么也不留,仿佛只是为了确认这里stillspeaks。
今晚也不例外。
当她们走近祭坛时,发现已有三人盘坐在废墟中央。一个穿着藏青色长袍的老妇人,双手交叠于膝,闭目如入定;一名年轻男子戴着耳机,正低声重复着一段听不懂的歌词;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外国老人,手里握着一支磨损严重的钢笔,在笔记本上疯狂书写,纸页随风翻飞,字迹却是清一色的东巴文。
陈露并未打扰,只是带着女儿在角落坐下。孩子熟练地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陶碗,盛满清水放在石盘边缘??这是她们的新仪式:每夜供一碗水,象征倾听的容器。
片刻后,老妇人睁开了眼。
她的目光落在陈露身上,没有惊讶,也没有寒暄,只是缓缓抬起右手,做了个古老的纳西礼节:掌心向上,三指微屈,如同托起无形之声。
“你听见了吗?”她用纳西语问。
陈露点头:“听见了。”
“不是现在,”老妇人摇头,“是十年前。你在大兴安岭唤醒水晶柱的那一夜,我正在玉龙雪山守夜。那天晚上,所有沉睡的鼓都自己响了三次。我们都知道,‘言种’醒了。”
陈露心头一震。她从未对外界透露过那次实验的具体时间,甚至连赵冉也是事后才知晓细节。
“你是谁?”她轻声问。
“我是最后一个见过你母亲的人。”老妇人声音低缓,却字字清晰,“她走之前,把一根骨笛交给我,说总有一天,她的声音会顺着孩子的喉咙回来。”
她说完,从怀中取出一支泛黄的短笛,通体由某种大型鸟类的翅骨制成,表面刻着细密螺旋纹。陈露接过时,指尖触到一处凹陷??那是牙齿咬过的痕迹,熟悉得让她瞬间红了眼眶。
小时候,母亲常在冬夜里含着这支笛子为她吹安眠曲。她说这样能让声音更暖,因为“气息要经过血肉,才算真正活过”。
笛子无声,但她仿佛听见了。
女儿悄悄凑近,伸手轻抚笛身。就在那一瞬,远处山谷传来一声悠长回响,像是风吹过岩洞,又像某种生物在低鸣。紧接着,七道不同方向的声音相继响起:藏族六字真言吟诵、蒙古长调起音、彝族海菜腔滑音、苗族芦笙颤音、阿拉伯祷词尾韵、非洲部落击节呼喝、还有……一段极像鄂伦春古调的旋律。
八声齐发,却不杂乱,反而在空中交织成一种奇异和声,仿佛大地本身张开了嘴。
老妇人喃喃道:“它在回应血脉。”
陈露猛然意识到什么,迅速打开腕上的录音仪。数据显示,此刻周围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极低频共振场,强度虽弱,但覆盖范围已达方圆二十公里,且正以稳定节奏脉动??就像心跳。
这不是自然现象。
这是**语言生命体**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