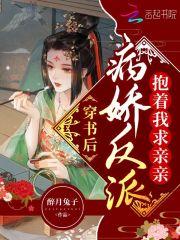笔趣阁>捡来的夫君他人美心善 > 新家(第1页)
新家(第1页)
“新出笼的肉包子嘞——皮薄馅大,一口生香!”
“油条——金黄酥脆的油条——”
五月下旬,日长夜短,晨露散去,小镇上最先开张叫卖的,总是那沿街而设的包子馒头、或豆浆油条早点小铺。
月芽在家中养了两日,这天清早便随萧巳出门。
两人进了镇上,在老张头包子铺前占了张小桌,随意聊了两句,穿着粗布短衫,肩上搭条汗巾的老张头端着新鲜出炉的包子来了。
“热腾腾的包子!四个猪肉馅的,四个素菜馅的,两位客官慢用!”
月芽先捡了肉馅的吃,怪道这家门前人客不绝,只咬一口那蒸得绵韧香软的白包子皮便知道大师傅手艺过人。
里头的汤汁还有些烫嘴,肉馅在口中滚了几下,试探地咬着竟有些沙沙的脆爽。
月芽眼睛都亮了。
真是好主意,竟在肉馅里拌了马蹄碎,那口滋味最是清甜,便是天热了吃多几个,也不觉得腻人。
她一连吃了三个,阿巳那头又给她递来一个素馅的。
月芽就着他的手咬了一口,才知道素的更鲜。
野荠菜独有的微苦味道被甜丝丝的红萝卜和香口的菌菇一中和,便只剩下了鲜味。
不过这应该是年前最后一口了,野荠菜最晚过了五月,天气渐热,就会变得酸苦,口感也粗糙许多。
月芽吃开了胃口,又是两个下肚,最后竟比阿巳还要多吃了两个。
这街边的包子铺主要是卖给来往过路的普通百姓,不像那酒楼里的吃食,做得精致,分量却少,这老张头实诚,一个包子就有巴掌那么大,月芽吃后才觉得有些撑了。
萧巳付了钱,转头看她在那对着吃剩的半个包子揉脸,小嘴一张一合的,好像在念叨什么,念叨完又一口吞了那包子。
正逢一个穿着半旧绸衫,留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骑着驴车经过,热情地向他招手:“萧老弟早啊!”
萧巳笑回:“杜老板。”
牙人杜老板的嗓门很亮,笑眯眯地说:“前儿跟你说的那间铺面空出来了,才收拾停当,这会儿就跟我去瞧瞧合不合心意?”
“好啊。”萧巳也应得很随和,牵了懵懵的月芽,乘着杜老板的驴车,三人一路往城南方向走。
“就是这了!”驴车穿过繁华的街道,最终在一处相对僻静的巷口停下。
杜老板一边领着人往里走,一边揣着手妙语连珠:“这巷名叫柳荫巷,说是百年前此地有一柳姓才子,尤其钟爱巷口的柳树,常在树荫下吟诗作画,或教孩童读书,后来他高中了状元,皇帝赏识,要赐他高官厚禄,他却不爱,一片赤子之心啊,只想回到家乡做个地方小官,济世安民,他曾作诗云:巷陌深深柳色新,绿荫深处是吾乡。后来,百姓们就用这柳荫二字作了巷名,叫此巷比别处都多几分书卷气啊!”
月芽两人随杜老板前行,沿途青石板路干净整洁,路两旁多是些小本经营的铺面,有针线房、杂货店、一家古旧的书肆,余下的便是一些小住宅。
此处距离镇上的市集还有两条巷子,虽不比主街繁华,但胜在安静,来往也有些行人,却又不至于太过喧嚣,正如那杜老板所言,自是另一番风雅。
三人在一扇褪色的老榆木门前停下,杜老板拿钥匙开锁,推来吱呀作响的门板,一股木质清香扑面而来。
只见门后便是前厅,空间不算很大,但格局清晰,正中的位置摆着一张长条形的柜台,角落里堆放好些木材,有的已经打成了桌椅的半成品,只剩上漆,有的只是简单锯了长短。
“主家原是做小家具生意的,后来儿子在外头经商发了财,便一家老小都搬到北边去了,托我寻个妥当人照看,因走得急,好些东西都没搬走呢,一应家具都是现成的,拎包就入住,萧老弟前些日子看了好几家都不中意,今儿这家看着可还行啊?”
萧巳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闹中取静,尚算合眼。”
杜老板一看那架势,就更卖力地推销,唾沫星子翻飞:“来来来,二位看看后头,前头做买卖,后头就是住家了,独门独户,清静又方便……”
穿过一道窄门,有个四四方方的天井,井旁种了一颗桂花树,树下有好几排花盆,有的里头还有未收割完的小白菜。
杜老板解释:“这家占地小些,没有园子,前主人就用这花盆种菜,取井里的水来浇,听说这井水又清甜又滋润,养啥活啥呢!”
再往天井后是三间相连的房屋,两大一小,大的可以做起居室兼卧房,小的可做厨房或储物。
萧巳不动声色地四处检查,尤其仔细看了看屋顶和墙壁有无漏雨的痕迹,心中已有了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