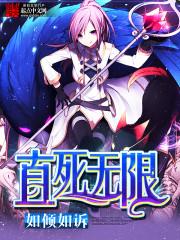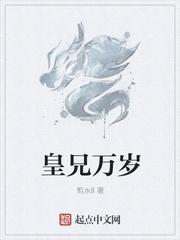笔趣阁>[柯南同人] 东京出走 > 第33章(第2页)
第33章(第2页)
“而因此伤害你们,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这段……感情也好,关系也好,我想只能走到这里了。”
“抱歉,是我任性。”
心平气和,分析利弊,坦诚布公,一些解决社交矛盾时常用的技巧,我用得轻车熟路,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我头也不回,仿佛有超脱世俗之外的冷静,放开贪恋的温度,一直向前。直到突兀地想起那个冬日的离家出走,那时我说我不愤怒,我仅仅是在思考,思考如何解决。但握在手里的手机外壳却皲裂出隙缝,掌心有麻木般的痛感。
这才品出一点微妙的难过。
可我没有时间难过,我很忙,繁忙的大脑需要清空那些混乱的情绪,动用理性的部分,思索周全的办法。警校只有半年,入职即上岗,我没有时间犹豫,我必须尽快成为明星。我有才华,有天赋,长相歌喉都出类拔萃,可那又怎么样,天上的繁星不计其数,不被投以注视的,只能泯没于尘埃。
所以我需要一个办法。
一个短时间内,快速积累人气的办法。
一个突破行业壁垒,让目光聚焦于此的办法。
一个一己之力,欺骗世界的办法。
联络的电话铃声划破空气,桌面的手机骤然亮起,经纪人的号码浮现在屏幕最顶端,我一跃而起,推开面前碍事的电脑,拿起手机,放到耳边。
“叶良,”对面的人显然难掩震惊,“你看到论坛上的——”
“是的,我看到了,请冷静下来,听我说。”
高悬的负重正逐步降落,脊椎窜过电流般的寒颤,徘徊多日的忍耐与紧绷感在颅骨内冲撞着,还不是时候,我对自己说,计划只差最后一步,还有一步就好。
轻轻呼出一口气,我站起身,克制着音量开口。
“反击的时候到了。”
成名
30。
事务所在北海道有间录外景mv用的录音棚。
我们连夜奔赴这处偏僻的取景地,顺手带上了仍然没能缓过神来的女孩。经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效率极高,两三个小时内就原地拉起了一支成熟的制作团队,从导演,收音,到摄影,造型一应俱全,其中不少人临时从本岛启程,预计明天上午抵达,而最关键的编曲团队则索性留在了东京,用电邮接收了我发过去的乐谱,过了一阵,回以录完的伴奏带。
“有点耳熟。”
松田在我点开确认时评价,眉间蹙起一点,似乎真的在用力回忆,我诧异地看他一眼:“你居然听得出来。”
“我听过?”他反应过来。
“凌晨三点听过,”我道,“但一直没机会问世,后来也改编了很多。”
在业界也屡见不鲜,档期,精力,个人风格,营销策略……能阻止一首歌正式问世的因素不计其数。更何况几年间我自己也数次重写这首曲子,却始终不够满意,它太独特,声音是传达的途径,可它代表的那个夜晚分明割裂,难言,又无处可诉。乐声流淌在车厢里,恍惚中是在讲述,有些情绪无法宣之于口,只能内化着自我排解。但当真消失不见了吗,还是在心底逐渐累积,成为高墙,生就语言无法穿透的隔阂。
“我喜欢这首。”女孩低声道,“它有名字吗?”
有的。
很多年前就定下的标题,只是无法对人诉说。
“它叫,《不可说》。”
我轻声答,拧头看着窗外,风雪银白,折射在视网膜上,很适合遮掩些什么。
车子在林海中飞驰,天际从暮色到深夜,晚上八点,我们抵达门口,一百平方米不到的仓库里塞满了幕布,打光板,麦克风支架,和各类被防尘布盖得严严实实的道具,光看外形比之废弃多年的工厂也不遑多让,似乎随时都可以拉去表演片场拍摄恐怖片,女孩下车时难掩震惊:这是录音棚?
对公众来说,是造梦的娱乐产业里最不起眼的一部分,我解释,对于我们来说,是工作时花费九成时间以上的地方。
“所以走吧。”我在她背上轻轻一推,“我带你去见真正的藤泽叶琉。”
比起舞台现场的激动人心,录音棚里的大部分工作是枯燥的,与录音师反复沟通选曲的风格和主题,敲定合适的声场,将声音调整到自己想要的波段和音色。虽然是早早备好的曲子,但实际打磨起细节才发现有许多未完善的地方,将完整的旋律分解成单节乐句,一句句反复找准情绪。毕竟是事件后的第一次露面,必定会赚足热点和眼球,经纪人要求按最高标准执行。整首歌录了接近五个小时,又是低音浑厚而感情饱满的曲风,我唱得大脑缺氧,总算被放出录音间时已是头重脚轻,站在门口缓了好一会,才找回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