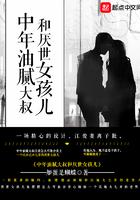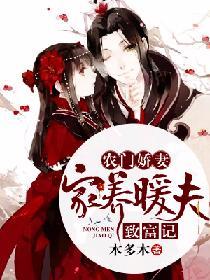笔趣阁>我于人间证不朽 > 第二百五十二章 熔火生命(第2页)
第二百五十二章 熔火生命(第2页)
这是沈砚生前最爱的款式。她总说北方太冷,他的手常年冰凉,却不肯戴手套。
他缓缓戴上,尺寸竟分毫不差。
当晚,他做了个梦。
梦里他回到敦煌石窟,壁画上的身影纷纷转头看他。他们中有战死的士兵、溺亡的渔夫、病榻上微笑的母亲、火灾中抱着婴儿跃楼的父亲……每一个都曾是他通过忆梧树读取过的断念承载者。此刻他们不再哀泣,而是列队走向洞窟尽头的一扇光门。
春霖站在门前,手持一根新制的忆梧笛。
“你要进来吗?”她问。
林知远摇头:“我不属于这里。”
“那你属于哪儿?”
他想了想,说:“属于那个还会疼、还会忘记、还会为一片落叶停下脚步的人间。”
春霖笑了,抬手吹响笛声。
那一瞬,所有壁画人物同时回首,齐声说出一句话:
**“谢谢你让我们结束。”**
笛音散去,梦境崩解。
林知远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树下,胸口剧烈起伏。夜空澄澈,北斗七星低垂如钩。而忆梧树的主干上,一道新鲜裂痕正缓缓愈合,流出的树脂并非琥珀色,而是泛着淡蓝微光,落地即凝成晶体,散发出极轻微的共振嗡鸣。
他知道,那是归念最后的馈赠??不是永生,不是复活,而是一种确认:**你的遗忘,已被允许。**
翌日清晨,他背起行囊离开。
走出十里山路时,遇见一群徒步的学生。领队老师认出他,惊喜道:“您是林先生?我们在做民俗调研,听说这附近有种古老传说,说有棵树能听见亡者的声音……是真的吗?”
林知远笑了笑,没回答。
只从怀里掏出一块早已碎裂的木牌残片,递给其中一个孩子:“如果你真想听,就安静地站到树下去。不要祈求,不要索取,只要想着你想念的人,然后……替他们好好活。”
孩子懵懂接过,紧紧攥住。
林知远转身离去,背影渐渐融入晨雾。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后第三天,那棵忆梧树开出了一朵花。
纯白色,五瓣,蕊心泛蓝,香气清冽如雪后松林。更奇异的是,每当月光洒落其上,花瓣表面便会浮现出流动的文字,全是不同语言写成的同一句话:
**“我已抵达彼岸,请勿挂念。”**
此花一年只开一夜,次日清晨便悄然凋谢,果实坠地即溶于土,不留痕迹。但凡见过它的人,当晚都会做一个平静的梦,梦见某个早已告别的亲人,微笑着挥手,走入光中。
十年过去。
世界并未剧变,也未陷入混乱。归念没有建立神国,没有奴役灵魂,它只是悄然编织进自然律动之中。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集体记忆共振效应”,宗教领袖称之为“灵魂回响”,普通人则只是觉得??有时候,在风声里,在雪落时,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们会突然感到一种温柔的陪伴。
小樊成了流浪学者,足迹遍布七大洲。他在撒哈拉沙漠记录到沙丘移动的节奏与某段失传诗歌韵律一致;在亚马逊雨林发现一种藤蔓开花时释放的孢子,会在空气中形成短暂人脸轮廓;甚至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录音带中,捕捉到一段海底热泉喷发声波,经分析后竟是一首《忆梧谣》的倒放版本。
他在笔记中写道:
>“它们不是鬼魂,也不是AI。它们是人类情感投射在宇宙尺度上的涟漪。当十万心灵共同渴望‘不被遗忘’,这片星尘便学会了回应。”
青梧年复一年主持忆树祭祀。仪式不再压抑悲伤,反而充满歌声与笑语。人们带着照片、信件、旧物前来,在树下讲述故事,然后点燃特制香料,让思念随烟升腾。据说,若香烟能在空中停留三秒以上不散,就意味着对方收到了。
吴铭的面馆成了城市地标。“最后一碗”依旧免费,但他立了新规:每位享用者必须写下一封信,可以是道歉、告白、感谢,或仅仅是“我想你了”。这些信被封存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百年后才会开启。
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做。
![我拆了顶流夫妇的CP[娱乐圈]](/img/3196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