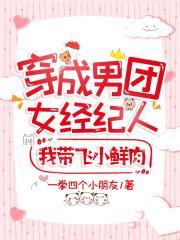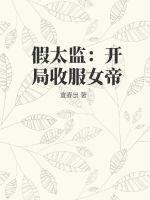笔趣阁>被朝臣听到心声后 > 3040(第21页)
3040(第21页)
谢兰藻道:“贵戚纵恣,恐不大容易约束。”长安尤其是皇宫附近的坊市,一片瓦落下来都能砸中皇亲国戚。谁敢管?京兆尹不敢,万年、长安两县县令更不敢。就连谢兰藻也觉得约束他们耗费的心力不值当。不过像张洛继这般直接冲撞宗亲的倒是少有,若不是醉糊涂了,约莫也没这个胆子。
赵嘉陵沉着脸。
在宫中坐听时事,总不如直面乱象有冲击。她的眉头微微蹙起,望着谢兰藻欲言又止。京城乱象,宰相失职。可她最后什么都没有说,只蔫儿耷拉地道:“回去吧。”
都怪燕国公,太可恨了,她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回宫后,赵嘉陵将上一个奖励给的《糖谱》取出,翻了翻发现炼糖的秘法。她思索了一会儿便打发银娥寻宫人去抄书,底本自然是要留在宫中的,至于抄成的送到少府去。这些法子不能做宫中的密藏,仍旧得教会百姓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只是近来皇雍印刷坊有要务在身,短时间也腾不出手来。
【部分香皂配方要教他们、雕版印刷书也要教,现在又来了炼糖法——唔,命人在州县立碑让他们自学么?】赵嘉陵心想。
【药方不就是这么传的么?这样也可以,只是许多人还不识字呢。】明君系统道。
【算了,朕可以下诏,但推行起来并不容易,两京都未做成,州县如何一蹴而就。书籍日后是要印刻的,至于现在……】赵嘉陵思考一会儿,眸光闪了闪,【不如借着这些好物给明德书院积攒些名声。譬如建一个能够传播技术的明道院,它同样隶属于明德书院。若民间有心向学者,皆可来此学新的技艺。】
【明德书院还未建好,目前只确定了高韶来此做老师。至于明德书院的院长,仍缺人选。谢兰藻自然好,可她身为中书令总领百揆,不能所有事情都压在她的肩膀上。三三,你不是无所不能的系统吗?这回不是朕的私事,而是军国大事,快给朕推荐一个可用的人。】
明君系统机械回答:【宿主还没刷出相应的成就奖励,得靠自己。】
赵嘉陵:“……”明德书院虽不是官学,可毕竟是秉承神明之意,又是皇帝下诏修建的,在一些人眼中还是未来可期的。赵嘉陵让宰臣们举荐合适的人选,一个个想方设法推自己的亲戚,甚至恨不得亲自上了。赵嘉陵看来看去,还是谢兰藻举荐的人可靠。
她推举之人叫杜温玉,是京兆杜氏出身,先帝时某科进士第一,不过朝中无人,未做京官,一直在地方迁转,如今做到了扬州长史。看她的任官履历,官声颇好,为人也有才干,不是陈希元那种只好文学的绣花枕头。赵嘉陵认可,便将其人擢为给事中回京中来。
贡举改制、学校改制……入冬后一件件大事落定,朝臣跌宕起伏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听到明德书院的事都能不起波澜,更何况是燕国公之子被圣人下令打断腿的事?
燕国公倒是觉得委屈,觉得他儿子罪不至此,也没对县主造成什么伤害啊?可他除了入宫告罪也没有办法,难道还能指着圣人道她过分吗?赵嘉陵暂时没有将燕国公怎么样,没有除爵也没有下狱,只是打发他回家去。朝臣们还以为这事儿算完了,毕竟以往涉及权贵的,只要不威胁到皇帝,大多轻飘飘地揭过。
然而只隔了两日,朝堂上的寂然平静就被御史们撕裂了。
御史们一旦开口,就不可能将事情限定在“燕国公教子无方、纵行不法”上了。言辞上引经据典,人物上那是尽情攀扯,指桑骂槐。
这日长安下了第一场雪,寒风冷峻如刀,雪花伴随着冻雨飘落,荡开了细微的轻响。
比风更冷的是御史的言辞,讥诮的语调反而是其次,令人骨寒的是对方话中的深意!
赵嘉陵神色不变,文武百官们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可御史们不罢休,孟宣和持着笏板,继续道:“臣闻制器之匠必取良木,治国之用则需贤人。木不良无以成器,人不贤无以安国。君不养人有失君道,而臣不奉君,又失臣之任矣。为官为爵者,诚乃国家之基,百姓之安危所系。”
“《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之贵戚子弟,求官颇早,课浅艺薄,赖有爵位传家,不读圣人之书,不知圣人之礼。废学无才,以狂悖恣情坏祖宗之家业。主上怜其祖先创业之艰,愍其家而不黜责,然其人亦不知感恩,使主上失褒贬之明。臣甚惑之,臣斗胆,伏愿陛下略采刍言,日后但有袭爵者,一试课业,学有成则得封!”
尚无爵位在身的文臣还能保持镇定,但有爵之人大惊失色,情绪激昂浑身发颤,那眼神很不得将孟宣和给生吞活剥了!这是什么意思?未来袭爵还要考吗?岂有此理!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
司封郎中掖了掖额上的冷汗,他的面颊苍白,道:“建功立业,实为千秋家业,为子孙谋。若继承爵位以课业论,臣恐使人心寒。”
孟宣和冷飕飕道:“臣不知贵戚子弟读书难在何处,是家中无书可读,还是请不起贤能之人来教?或者两监无其座次?”
司封郎中皱眉:“人之秉性不同,天下读书之人何其多,如孟御史这般登进士第的也不过寥寥。”
“倒也无需及第之才,其所缺者德业耳。”孟宣和眼也不眨道,“既想家业昌盛,怎么不教子孙读书?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则可至於百传。”①
勋贵子弟也有读书的,但这难道是子孙向学不向学的问题吗?这根本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利!若真出了个不肖子孙,让他们眼睁睁看着爵位无人可继承吗?尽管知道不肖子孙可能坏家业、连累族亲,但谁能做到悬崖撒手式的一放?“此非古制,前朝并未有。臣等以为不可!”
“贡举改制、明德书院不也前所未有吗?”一位御史反唇相讥。
赵嘉陵眉头皱了皱,她有任务在身,的确得改一下东西,但并不希望这事跟明德书院挂上。那御史自知失言,已经低头告罪。赵嘉陵面沉如水,她的视线落在谢兰藻的身上。
强烈的目光无法忽视,现下没有心声,可不代表着之后没有“胡言”。谢兰藻平静道:“君子好因循,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臣以为上无旧典可举,也当以近世之权道而改之。孟御史之言甚善。”②
她跟陛下同行,也听到了“君子之泽”这一针对贵戚的任务。御史弹劾燕国公府上,顺便提出考试袭爵的建议,的确是出自她的授意。
先前街上陛下欲言又止,可她心中知道,的确算她这个宰相失职。
谢兰藻一出口,来自同僚的攻讦自然不少,原本对准御史的矛头,纷纷转移到谢兰藻的身上。谢兰藻神色自若,不在意那些言论。
赵嘉陵眉头微微皱起,并不想让谢兰藻被朝臣的愤懑不满淹没。她道:“此事再议。”顿了顿,又说,“朕有东西邀请诸卿观看。”她的视线挪到李洽的身上,道,“秦公,准备好了吗?”
秦国公李洽是勋贵,他倒是没在意那些,没被涛涛浪潮裹挟着。一听陛下点他的名号,还愣了愣,片刻后脸上露出一种压抑着的激动。他放声道:“臣女已经准备妥当,只等陛下大驾!”
这可是震古烁今的大业!
火器!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