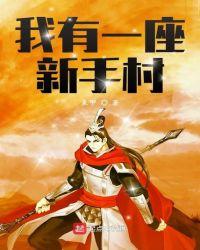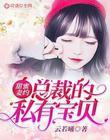笔趣阁>被朝臣听到心声后 > 7080(第5页)
7080(第5页)
“这想要打碎流内和流外的界限,还得有很长一条路要走。”赵嘉陵私底下对着谢兰藻感慨。流内、流外完全是两个系统,有它们各自独立的晋升渠道。流外官可以转入流内,但走到三省的主事,担任个七八品的小官就到头了,一些清望官根本不允许流外的胥吏们染指。这种社会风气使得赵嘉陵没法直接下旨,毕竟这得罪的是整个士群。
“如今只能稍作整顿。”谢兰藻道,流品莫贱于吏,在士人的眼中,此辈心术已坏,不可与士人同列。在太宗时曾有中书省书吏参与贡举,等到及第后,太宗直接追夺那书吏所受的敕牒,谓走吏冒进,贡举之设,为士流而设,不许走吏窃取科名。虽然太宗没有下诏明确禁止胥吏应举,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道阻隔胥吏的线。
跟赵嘉陵提了太宗朝的旧事后,谢兰藻叹息一声:“流内流外之分得随着明德书院、贡举改制一道推动,而这些,最需要的便是时间。”
赵嘉陵抱怨道:“祖宗太不识大体,现在却教朕为难。”
谢兰藻:“……”这话就不是为人臣的能接了,她道,“‘水泥’足以见证明德书院的大用,到了明年,陛下或许能下诏州县修书院。”也许不用明年,等到书刊、学报将消息送到州县,有点心思的恐怕会走到前头,不等诏令到便开始建书院了。毕竟,印刷术推行后,教学之用的书籍,也不是什么秘密。
赵嘉陵突发奇想:“两监通过考核的监生能直接参与省试,那明德书院呢?能如国子监吗?学生若参与贡举,会有人反对么?”
谢兰藻眉头蹙起,贡举改为三年一次,下一回得在天符八年。时间有些紧,但陛下有神明相助,也未必不可能。思忖一阵后,她如实道:“这得看明德书院的分量有多重了。”
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赵嘉陵闻言一下子振奋起来,她一扬眉,洒然笑道:“那就当作一个伟大的目标,朕与你约定,争取*下一轮贡举让明德书院的学生走到前边。”
谢兰藻肃容,她注视着赵嘉陵的笑脸,而后朝着她俯身一拜:“臣定不负陛下!”
赵嘉陵喜上眉梢,她“嗳”一声,又道:“口头说说么?你题字落印,朕要请人裱起来。”
真要题了字,她表忠义之心,绝对会扭曲成另一种样态。谢兰藻一看就看穿赵嘉陵的那点小心思,她一颔首,面上浮现微微的笑意,问:“陛下还要臣写别的吗?臣好一道写了。”
意料之外的答案让赵嘉陵呆滞了,在关键时刻,终于没继续当愣头鹅,脑筋一转,急中生智说:“那你看着来?”问题丢给谢兰藻了,让她自个儿发挥,最起码能捞到一张“不负”,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不争气错失良机吗,落得一个两手空空。“你在这儿写吧,朕让银娥去准备纸笔。”赵嘉陵又说。
说吩咐就吩咐,那架势仿佛怕谢兰藻反悔。
纸笔到了,赵嘉陵亲自磨墨,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盼着谢兰藻能够满足自己那股说不清的期待。在赵嘉陵失神间,如行云流水的六个字已经落到纸上了。
“陛下真没有想法吗?”谢兰藻问。
赵嘉陵在侧边,她凝视着谢兰藻清隽的脸,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泠然如秋月的,甚至有些冷漠。但此刻,从她的眉梢捕获到的是融融的笑意。盯半晌,她眨了眨眼,迟缓的思维忽然间灵活过头了,脱口就说:“那就‘大明春深锁中书’。”
谢兰藻眼皮子一跳,她看也没看赵嘉陵:“陛下的弘誓大愿呢?少看些闲书好。”
赵嘉陵的思维跟旁人不同,她“啊”了一声,扬笑道:“你也看过了啊。”
谢兰藻不想理她。
赵嘉陵讪讪地笑着,她承认一时失误,这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她的视线往纸上落:“报答君恩知有处——嗯?怎么不继续?”
谢兰藻凝着她,笑问道:“陛下以为如何续呢?”
赵嘉陵:“清宵低语到更阑?”
第74章
字幅留下来陪赵嘉陵过漫漫长夜了,至于人,在扬唇一笑后,飘然离去,只余下缥缈绝尘俗的身影在赵嘉陵心间伴着一点怅然无尽徘徊。
【她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就算有了一个惊喜在前,赵嘉陵也没想着谢兰藻真的会按照她说的落笔,连点曲折都没有。她都做好了谢兰藻推脱的打算。
【可能觉得比“大明春深锁中书”好吧,宿主,你成功地拉低了她的下限。】明君系统幽幽地说。
赵嘉陵不听:【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转念一想,追究缘由也是没必要的,总归是件喜事。她伸了个懒腰,洋洋得意,【朕就是要做这样的皇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明君系统:“……”
整顿县官和胥吏的事,在议论几天后,仍旧按照旧制去做了,派遣监察御史巡视州县,以正风俗。谢兰藻的提议也得到了宰臣的认可,稍微提了胥吏的待遇,不让他们再做白工。但员额上,却做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县衙里的正员可以用。这也是防止县衙漫无拘束地任用“胥吏”,借此事敛财。
八月的长安还算安宁,水泥路的建设有序地从南往北推进。明德书院中除了工学的学生弄出了“水泥”外,农学那边也有了喜人的成果。六月奉命种下的植物种子,有一部分蔬菜已经可以收获果实了。虽然暂时比不上“水泥”,但这还没完呢!等到十月番薯成熟后,那产量一定可以让人刮目相看。
学化学的跟工学的待在一起,继续钻研水泥;律学呢,已经出了学报,在将大雍的律法宣扬出去上立下大功。医学生们妙手回春,弄出了很多胜似仙丹的药,还消杀了炎炎夏日沟渠里的蚊虫;农学也切切实实地收获了,就剩下——
“就剩下咱们了,文学,唉。”这也不怪学生们唉声叹气了,昔日的旧影盘桓不散,让文人的心中多少有点自负。当然,现在那点趾高气扬在遭遇一重重的打击后,完全烟消云散了。“难道文学真无用?”
“诸位也别妄自菲薄,学报也是咱们帮忙润色的呢。”青衿士人回答道。可话一出口,学生们的神色变得微妙起来。“润色”一开始没那么顺利,他们有足够的才情,落笔生活。但洋洋洒洒好一宏篇大论,不仅没能博得夸耀,反而被无情地打回来。
律学生说:“学报是面向大众的,骈四俪六,谁听得懂啊!”
“诗也有诗的神妙,想要秉笔中书,那会掘土是不够的。”说话的学生清了清嗓,“教坊司那边要人写那什么剧本,谁要来帮忙?”
跟教坊司那边连线是裴无为的主意,由薛元霜提出的。
裴无为说:“识字的人有限,想要靠学刊学报深入乡里,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但走街串巷的百戏就不一样了。”她虽然出身士族,但对仕途兴致寥寥,年少时便离乡四处游历。她潇洒不拘,颇为轻狂,跟三教九流的都能打成一片,视野自然比闷头读书的要开阔。
薛元霜便以明德学士的身份与书院中的人谈了。她一直忙着跟陈希元她们一道编修礼书,许多事情都是去那边凑热闹的裴无为告诉她,蹙着眉头一琢磨,颇为有理。
教坊司是仁宗时设立的,仁宗皇帝酷爱歌舞,置左右教坊司,在光宅、延政二坊中。先帝与今上都无意曲乐,只在有大宴的时候请教坊司诸乐官表演。先帝时稍有裁抑,并为官员请教坊乐工表演制定严格规矩,不许官员欺凌诸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