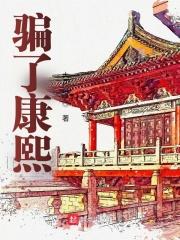笔趣阁>被朝臣听到心声后 > 8090(第11页)
8090(第11页)
乍一听“天道”两个字,赵嘉陵一哂。她漫不经心道:“先前诸位也发了愿心,愿意来分担灾祸。怎么天道不怜诸卿?未见祥瑞眷顾?难道是诸位心不诚吗?”她这番诛心的言论说得很轻巧,先前发愿心的朝臣被砸得直不起腰。怎么麒麟就眷顾谢中书呢?天恩浩荡,是爱陛下所爱吗?
劝阻的声音低了下去,赵嘉陵满意了。
安静数息后,谢兰藻又建议今岁开制举,至于名目,与“农田沟渠水利”事相关。河南旱灾蝗灾重,农学生那边提出要改善水土,趁着这个时候选拔人才,一来是给非书院出身之人一个机会,二来也是让书院中早能独当一面的人走到前头来。她还道:“臣以为,应制之人不设限,各色人等,但有才能,皆可报名应试。”
朝臣能说什么呢?只能应和。先不说现在的谢中书是日中天,单是看“制举”,他们也没理由阻拦。各色人等这点不符合旧制,然而不符合的地方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陛下说了算?制举那是全凭陛下心意啊。
“等到制举选出合适的人后,直接依照才能来任官。”朝会结束后,谢兰藻在赵嘉陵议论。朝廷的三省六部在州县也有相应的职务,过去哪里能分得那般细致?士人们只把那些小官当作上进的阶梯。现在么,阶梯的作用还是有的,然而有些东西需要变化了。再过几年,等到时机合适了,那些小吏也需要变,得将他们真正纳入系统中来,取缔一些地方父子亲戚连任、独霸一方的现象。
“虽然有了波折,但还是稳中向好的。祭祀太庙的时候呢,也有功绩可以交待了。”赵嘉陵眸光粲然明亮。先帝诸子中,她跟四姐最不被先帝看好,四姐是疯癫,她是愚钝,可只有她跟四姐好好的。这说明先帝的眼光十分有问题,先帝若地下有知,该向祖宗忏悔。
“对了,我还与祖宗说了我们的婚事,祖宗没有跳出来反对。”话锋陡然一转,赵嘉陵美滋滋地笑着,她注视着谢兰藻,又说,“先前是谁递上了折子,我忘记了,怎么不再递一回?”
谢兰藻:“……”要是祖宗能跳出来反对,那问题就大了。灿烂的笑容感染人,谢兰藻的心也跟着赵嘉陵的语调一道飞扬了。那人她倒是能够记得名号,只是先前考绩不过关,早已经被打发到京城外了。
“民间正在热议麒麟呢,一些书籍大有市场,该趁热打铁了,你与我是天作之合。”赵嘉陵托腮,她朝着谢兰藻眨了眨眼,满含期待。
谢兰藻莞尔道:“时机到了,自然有人会上请。”不过这个“时机”也是人为造就的,铜匦不就是让人投书的么?至于投书的人,其实也不难找着。
“你的意思是答应了?”赵嘉陵露出讶然之色,谢兰藻能想到的她当然也能想到,只是心中有所顾虑。不过要是能得到谢兰藻的首肯,她要第一时间着银娥去办。
“臣还有其余选择吗?”谢兰藻瞥了赵嘉陵一眼,慢条斯理问。
“没有没有。”赵嘉陵赶忙摇头,连声否定道。她哼了一声,将谢兰藻往怀中一揽,骄傲地挺了挺胸,宣布道:“除朕之外,别无选择!”
回到长安的第一个夜,赵嘉陵放谢兰藻回家见亲人,但这第二个晚上,赵嘉陵不会放人,只想与谢兰藻尽情温存。
寝殿中,伺候的人一一退下了。
火烛摇曳着,映衬着如莹玉般的面庞,添了几分娴静。
谢兰藻只着了单衣坐在床上看书。
赵嘉陵没有谢兰藻这等好学的心,她盘腿坐在谢兰藻对面,手肘压在腿弯,双手托着面颊看谢兰藻,似是怎么都瞧不够。
不过这点耐心随着窸窸窣窣的翻书声,到底还是渐渐消散了。赵嘉陵装模作样地嗳了一声,说:“不信你在道上想我了。”她这么大咧咧坐着呢,都不见谢兰藻深情注视。
谢兰藻面颊微红,有一点情怯。书页翻了又翻,到底有多少能入眼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将书放到了一边,她看着赵嘉陵抻直双腿,不由问:“怎么了?”
赵嘉陵说:“麻了。”
谢兰藻狐疑地看着她,这才多久便麻了吗?可心中想归想,人还是凑上前。只是才靠近,赵嘉陵的笑靥就在眼前放大了,她被赵嘉陵一拉,跪坐在她的腿上,双手则是撑着她的肩膀,两人面对面。
赵嘉陵伸手揽着谢兰藻的腰,埋首吸了口气,笑着说:“又好了。”她的眉眼飞扬,眸中传达的意思很是明显了。谢兰藻抬手拨了拨额前的发丝,轻声道:“帐幔。”她作势要起身,可赵嘉陵眼疾手快抓住她,不让她动弹:“又没人瞧见。”
谢兰藻微微蹙眉,这可不是帐中小灯,月光、烛光、烟光交织,风来水晶帘动,心中总有种奇妙的感触。她向来端肃,但现在被陛下引着越来越出格。
赵嘉陵仰起脸看谢兰藻,央求她说:“就一回。”顿了顿,又可怜巴巴说,“你这一走就是数月,许久不见,只想好好看你。”
谢兰藻睇她:“只是看么?”
赵嘉陵坦诚说:“不止。”她在谢兰藻的下巴上亲了下,“但不能缺了这一环。”
谢兰藻吸了吸气,在赵嘉陵楚楚可怜的视线下屈服,她压住了那点难为情,抿着唇很小幅度地点头。
赵嘉陵高兴了,吻就像是雨点般落。灵活的手在谢兰藻的腰间游动,解开了系带,却未将它退下。谢兰藻被赵嘉陵亲得有些恍惚,好一阵后,才猛然间醒悟,赵嘉陵的“不怀好意”比她想得还要多。赵嘉陵压根没打算躺下,只维持了最初的姿势,伸手开始拨弄。这视线一往下望,就能瞧清她到底在干什么!
谢兰藻的面颊蹭得一下红似火,她想要起身,但赵嘉陵一只手有力地揽着她的腰。而她胡乱扭动,俨然也是将自己送上,才提起了一点力气,整个人又软了下来,趴在赵嘉陵的肩上。她咬着唇,遏制住了低吟,只是抖动间不免溢出几道喘息。
赵嘉陵开始胡言乱语:“你都不看我,不珍惜我。”
谢兰藻不想理她,床帷笼住的小天地里烛光是幽暗的,哪像现在。险恶用心原来是用在这里,根本不是想在灯火中看她的脸。她要是抬头,眼角的余光很难不游走。她不说话,按捺不住的时候,就在赵嘉陵的肩上咬一口。
许久后,谢兰藻微微抬身,这床帷敞着,有凉风吹过。谢兰藻微微一瑟缩,无力地坐在赵嘉陵的腿上,她伸手合拢中衣,微微遮住了身躯。面颊上的红晕汹汹,还没到褪去的时候,连瞪视赵嘉陵的眼神都有些绵软无力。
赵嘉陵问:“热吗,要擦擦吗?”
先前吃过的亏谢兰藻还记着,她不信这句话。
赵嘉陵又说浑话:“不用手,用腿。”长夜漫漫,如何教人睡去。锻炼带来的体魄还是足够强健的,就算坐着个人,抬起腿来也不费劲。“想你的时候,我就看书。”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她搂着谢兰藻,灼热的视线在雪白圆润的肩头流连。
谢兰藻羞恼的瞥她,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力气,用来推人了。赵嘉陵揽着她倒向被褥里,她眼睫颤了颤,对上赵嘉陵那黑曜石似的眼眸,手肘压了压她,嘶声道:“躺着。”
赵嘉陵想使劲浑身解数,但考虑到谢兰藻的心情,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了。她拥着谢兰藻,咬着她的耳朵说:“太矜持。”
谢兰藻假装没听见,这人先是没胆,然而得到应允后就放开了,纵情肆意地胡来。至于她自己——只是在失控的沉沦中,有点不知所措。她抿了抿唇,最后低声说:“需要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