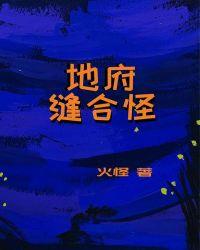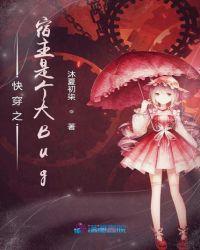笔趣阁>婚后上瘾 > 第373章 陆 魏 腰不好(第2页)
第373章 陆 魏 腰不好(第2页)
“他很特别。”聿战低声说,“比我想象中勇敢得多。”
“他是从你的沉默里学会坚强的。”袁晨曦望着儿子的背影,“你不在的日子里,他总问我:‘妈妈,爸爸是不是不喜欢听不见的小朋友?’我说不是,是他还不懂怎么表达。然后他就开始画画,画很多会飞的东西,说要替爸爸把话说出来。”
聿战的手猛地攥紧了膝盖上的布料,指节泛白。良久,他才哑声道:“我会用余生去学。”
这时,念安跑了过来,手里举着一张刚画完的画。纸上是一棵大树,树根深深扎进泥土,枝干向上伸展,分成三根主枝??一根牵着母亲的手,一根握着父亲的手,中间那根托着一个小小的风筝。
“这是我画的家。”他说,把手语打得格外清晰,“树不会说话,但它一直在生长。”
袁晨曦接过画,眼眶微热。她看向聿战,发现他的眼角也有湿意。
“你想贴到集体风筝墙上吗?”她问念安。
“嗯!”孩子用力点头,“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家!”
三人一同走向那面由百幅儿童画组成的“希望之墙”。当念安踮脚将画贴上去时,其他家长纷纷投来善意的目光。有人认出了袁晨曦,悄悄举起手机拍下她的侧脸,却没人打扰这份宁静。
傍晚时分,人群渐渐散去。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风筝一只只落下,唯有那只银白色的仍在空中盘旋,仿佛不愿告别。
“它还能飞很久。”念安仰头笑着说,“风还没停呢。”
聿战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递给袁晨曦:“这个……本来想等听证会结束后再给你。但现在我觉得,或许你该早点知道。”
她迟疑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本手工装订的日记簿,封面用烫金字体写着:《致晨曦》。
翻开第一页,是他的字迹:
**“2013年4月7日,晴。今天在董事会上否决了并购案,因为对方公司涉嫌压榨女工。同事说我变了,可我只是想起了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权力不该用来碾碎弱者。’”**
第二页:
**“2015年冬,雪。我去了你住过的庇护所,站在门口站了两个小时,没敢进去。管理员告诉我,有个女人总在夜里教孩子们折纸飞机,说那是‘逃出去的船’。我知道是你。”**
第三页:
**“2018年春,阴。我查到了你们的行踪,但最终没去找你们。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怕你眼里只剩下恨,而我已经承受不起。”**
一页页翻过去,全是这些年他独自写下的忏悔、思念与自我拷问。没有辩解,只有记录。最后一页写着:
**“如果你愿意读到这里,请允许我重新认识你,不是作为受害者,也不是作为孩子的母亲,而是作为袁晨曦本人。我想了解你喜欢的书、讨厌的气味、害怕的梦境,以及……是否还喜欢春天。”**
袁晨曦合上日记,指尖微微发颤。她没想到,那个曾用合同和条款定义一切的男人,竟会以如此笨拙而真挚的方式,一笔一划重建一座通往她内心的桥。
“这些……都是真的?”她问。
“每一个字。”他直视她的眼睛,“我没有奢望你立刻接受,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不是在表演悔改,而是在努力成为一个配得上‘父亲’这个词的人。”
她深吸一口气,将日记收进包里:“我会看完它。”
这句话虽轻,却像一颗石子落入深潭,在聿战心中激起层层涟漪。他嘴唇动了动,终究只化作一声低低的“谢谢”。
回家的路上,念安在后座睡着了,怀里仍抱着那幅全家树的画。车窗外夜色渐浓,街灯次第亮起,映照出城市温柔的一面。
袁晨曦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流动的光影,思绪纷飞。她想起十年前那个蜷缩在桥洞下的自己,也曾以为人生就此终结。可命运终究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不是逃离,而是面对;不是复仇,而是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