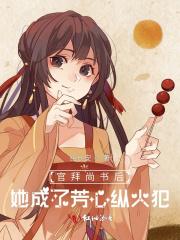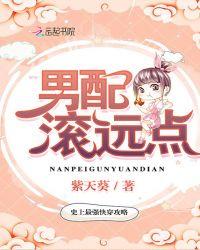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我是县城婆罗门 > 第375章 财富金币被叫停(第4页)
第375章 财富金币被叫停(第4页)
同时,她写信给联合国伦理委员会,建议将“数字代语权”纳入全球数字人权框架,明确提出:“任何人,无论生死,其声音表达必须基于真实存在或明确授权。否则,即是冒犯。”
信件引发国际热议。多家媒体称她为“数字时代的守夜人”。
但她不在意这些称号。
她只在乎每一次按下录音键时,是否对得起那份托付。
四月二十八日,移动驿站完成第九站任务,即将返程。途中经过一片开阔草甸,远处传来悠扬牧歌。
扎西忽然停车:“看,是达瓦家的牦牛队。”
果然,十二头牦牛正缓缓穿行,达瓦骑在一匹老马上,背影挺直如松。他远远望见车队,挥手示意。
沈安安下车迎去。
达瓦从怀中取出一个小木匣,递给她说:“这是我让村里的匠人做的。他说,这种盒子,以前是用来装经文的。”
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雕刻精致的骨笛,正面刻着一行藏文:**愿你的声音,渡尽孤魂**。
“我们不懂科技。”达瓦说,“但我们懂思念。你们做的事,就像古老的招魂仪式。不一样的是,你们能让魂归来时,带着笑容。”
沈安安双手接过,深深鞠躬。
返程路上,她将骨笛轻轻挂在“声音方舟”的后视镜上。每当车辆颠簸,便会发出细微清鸣,与车顶风铃应和成韵。
五月一日清晨,车队回到措美县。居民们早早聚集在小学门口,手持哈达与酥油茶,像迎接归来的亲人。
卓玛拉措也在人群中。她拄着拐杖,却站得笔直。见到沈安安,她颤巍巍走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
翻译展开读出内容:
“这是我写给儿子的新年信。去年我说完了回忆,今年我想告诉他:阿妈很好,村里有了会唱歌的房子,我每天都去坐一会儿。你放心,我会活到一百岁,替你多看看这个世界。”
沈安安接过信,郑重放入恒温箱最上层。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这项事业的意义,从来不是对抗死亡,也不是复活过去,而是让活着的人,学会如何带着爱继续生活。
当晚,她坐在工作站写下日记:
>“今天我们带回了九段新录音、三封未寄出的信、一个少年的第一声‘妈妈’,以及一颗不再逃避的心。
>
>我曾以为,声音是记忆的容器。
>现在我知道,它是桥梁??连接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孤独与理解。
>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出最后一句话。
>而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这句话,不会消失在风里。”
窗外,风铃轻响。
像一声声温柔的应答。
像一句句永不终结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