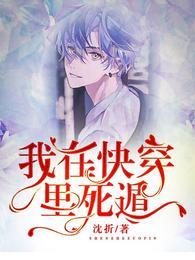笔趣阁>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57章 请陛下赐臣一死(第1页)
第457章 请陛下赐臣一死(第1页)
皇宫,御书房。
烛火通明,将室内映照得亮如白昼,却驱不散那几乎凝为实质的沉重压力。
禁军统帅南宫?与廷尉府总督丁爻正襟危坐,身体僵硬,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二人目光低垂,只能偶尔用眼角的余光,飞快地瞥向御案之后那尊贵的身影。
大周天子,周承渊。
年过五旬,两鬓已染秋霜,此刻正默然端坐,他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紫檀木御案,每一下轻响,都仿佛敲在南宫?与丁爻的心头。
一股无形的帝王威压弥漫开来,。。。。。。
风卷残云,春雷未歇。万忆塔第一百层水晶般的光晕尚未散去,那滴悬浮于空的心镜之水,竟在某个子夜悄然裂开一道细纹。无声无息,却仿佛天地俱震。
次日清晨,守塔弟子发现塔基密室墙上多了第三行字,墨迹如新,似以血为引:
>“路已通,门将启。”
无人知晓是谁所书,可那笔锋转折之间,分明带着陈七早年刻碑时特有的顿挫之力。更奇的是,自那一日起,全国各地的忆碑开始同步低鸣,音调不一,却逐渐汇聚成一种古老旋律??正是《守心录》开篇的诵调,只是节奏缓慢三倍,如同亡魂踏着时光回返。
与此同时,九条“忆脉”线路再度震动。
朔州残碑前,一夜之间长出九株蓝莲,花心泛金,根系深入冻土三百丈。有拾忆人冒险掘开地底,竟触到一块巨大的青铜板,其上铭文赫然写着:“冥枢九钥,归于一心。”而当他们试图搬动铜板时,整片荒原忽然响起战鼓声,虚空中浮现出千军万马的轮廓,皆披重甲,面朝北方,静默列阵。
幽州托梦井则彻底干涸,井底露出一条向下的石阶。拾忆队持灯而下,行至百级后进入一座地下宫殿。四壁绘满壁画:第一幅是皇帝亲赐旌旗,将士跪接;第二幅却是同一支军队被围困山谷,箭雨如蝗;第三幅最为惊心??一群戴枷囚徒被推入深坑活埋,而监刑官袍角绣着龙纹。
最令人窒息的是最后一幅:一名女子立于高台之上,手持铜铃,身后站着一个背铁铲的男人。两人目光穿透画壁,直视来者。画旁题字仅八字:“若忘我名,山河代记。”
凉州青铜匣自动开启的消息传至长安时,正值御史巡边归来。匣中并无文书,唯有一枚玉印,印纽雕作双首蛇相噬之形,印文阴刻:“承罪司命”。史馆老学士颤抖着翻检古籍,终于在一部禁毁残卷中找到记载:此印乃前朝设立“冥枢机构”时所铸信物,专司掩盖战败、抹除阵亡者姓名之职。得此印者,可调动隐吏三千,专事焚档灭口。
“原来……我们一直在替罪人书写历史。”老学士伏地痛哭。
而在苗疆耳山深处,那处曾出土童骨的溶洞突然闭合,岩壁渗出血色液体,凝成一行象形文字:“祭品已足,请还命簿。”拾忆女队首领当即割腕滴血于石,以巫语回应:“吾等非取债而来,乃携光同行。”话音落,洞内骤亮,一幅由磷火构成的地图缓缓浮现,标注着第十个地点??不在人间版图之上,而是标注为:“心渊?倒影城”。
这十地连成一线,恰与万忆塔顶铜镜投影的星轨完全重合。
民间议论沸腾之际,朝廷内部亦起波澜。抚忆司主官连夜上奏,请求彻查“承罪司命”相关档案,却被内阁压下。新任首辅虽仍供奉陈七画像,但近来神情恍惚,常于深夜独坐书房,反复抄写《守心经》中一句:“知其所蔽,方能破妄。”
某夜暴雨倾盆,他突命仆人焚毁所有藏书,只留一幅空白卷轴悬于堂前。翌日清晨,仆人在地上拾到半片烧焦的纸屑,上面残留数字:“七十三……万人……未录名。”
与此同时,敦煌藏经洞的朱砂地图再次显现异状。原本标注的九处地点光芒渐盛,而“冥枢旧址”四字竟缓缓褪色,化作五个新字:
>“在你心中开。”
游方僧人闻讯重返莫高窟,叩钟七昼夜。第八日黎明,第十七窟壁画中的飞天忽然转首,指尖指向西方极远处的一座沙丘。当地向导冒险前往,挖出一口锈蚀严重的铁箱。箱内没有遗物,只有一面小镜,镜背刻着一行小字:“照见自己,即见众生。”
消息传开,各地拾忆人纷纷取出随身携带的忆笺,在月下点燃。奇迹发生了??以往自燃的忆笺只升青烟,如今竟在空中凝成短暂人影,或挥手,或颔首,甚至有人清晰复述生前最后一句话。陇西一位老妇烧掉亡夫临终遗言后,次日清晨发现院中梨树开出红花,花蕊中嵌着一枚早已丢失的铜钱,正是当年定情之物。
人们终于明白:记忆不再是单向追思,而成了双向奔赴。
然而,真正的变局始于归语村。
那个写下《初心》的小女孩已长大成人,成为新一代拾忆导师。她在教授孩子们书写祖辈故事时,发现一名少年始终沉默。追问之下,少年颤声说出家传秘密:其先祖曾任“承罪司”基层吏员,负责销毁阵亡名单。临终前留下遗训:“吾族之罪,不可洗,唯可赎。若有蓝莲开于坟前,方可安眠。”
女孩听罢,带领全村孩童在其祖坟四周种下蓝莲。三年过去,寸草不生。第四年春,一场暴雪过后,坟头竟破土而出一朵纯黑之莲,花瓣边缘泛着幽蓝微光。当晚,少年梦见无数士兵从雪中走出,每人手中捧着一张名单,最前方一人递给他一本册子,封面写着:“朔州七十三万殉国录”。
醒来后,册子真在枕边。
册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位战死者姓名、籍贯、功绩、死因,甚至包括他们最后的愿望。有人想再喝一口家乡井水,有人盼妻子改嫁,有人只求死后名字不要被除籍。而统领这支大军的主帅,赫然是李守忠??那位冰封古墓中的朔州守将。
更惊人的是,名录末尾附有一段批注,字迹与陈七年轻时极为相似:
>“我不是将军,也不是英雄。
>我只是一个不愿忘记的人。
>若你们读到这些名字,请替我说一句:
>‘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