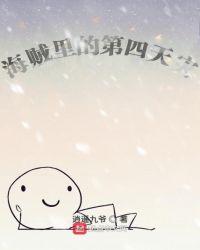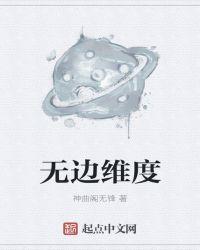笔趣阁>去父留子后才知,前夫爱的人竟是我 > 第383章 宁愿不要这份血缘关系(第3页)
第383章 宁愿不要这份血缘关系(第3页)
他坐在琴前,指尖轻触黑白键,缓缓弹起那首熟悉的摇篮曲。音符流淌而出,温柔而坚定。
弹到一半,电子竖琴忽然加入合奏,随后是远处共频舱传来的轻微嗡鸣,接着,屋顶花园的铜铃轻轻晃动,仿佛有看不见的手在拨动。
念念推着轮椅进来,爬上他的膝盖,小手覆在他的手上,一起按下最后一个和弦。
房间里寂静无声。
良久,投影仪自动启动,浮现出一段从未见过的画面:年轻的苏文澜抱着仿真婴儿,轻声哼唱。而在她身后虚空中,隐约可见一个少年身影静静伫立,目光温柔。
少年嘴唇微动,无声地说了一句什么。
林清漪调出唇语识别程序,结果跳出三个字:
**“谢谢你。”**
程砚舟闭上眼,任泪水浸湿脸颊。
他知道,这三个字,不只是对苏文澜,也是对他,对夏南枝,对每一个曾为阿渊点亮灯火的人。
第二天清晨,疗愈中心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张合成图像:南极冰原上,极光如幕布般垂落,照亮了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脚印始于远方,终于一处平坦雪地。在那里,两个影子依偎在一起,一个高大,一个瘦小。
图片下方写着:
**“他们终于见面了。”**
夏南枝抱着念念站在雕塑《听见》前,阳光洒在三人身上。小女孩仰起脸,忽然开口,声音稚嫩却清晰:
“妈妈,哥哥说,他很开心。”
夏南枝浑身一震。
“你还记得哥哥的样子吗?”她轻声问。
念念摇头,随即又点头:“我看不见他,但我能听见他在笑。”
那一刻,风吹过薰衣草田,带来遥远而温柔的回响。
程砚舟站在山坡另一端,望着这一幕,缓缓摘下腕表,放入纪念室的捐赠箱中。
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
**“给未来的爸爸。”**
他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执着于科学逻辑的医生,也不再是困于失去之痛的父亲。他是见证者,是传递者,是千万个听见爱的声音之一。
几年后,《静默者的语言》被改编为音乐剧,在百老汇首演。谢幕时,舞台中央升起一座透明水晶模型,里面漂浮着无数闪烁光点,象征每一个因阿渊而发声的灵魂。
观众席中,一位白发老人默默起身,将一朵干枯的薰衣草放在座椅上离去。花旁留着一张字条:
**“阿渊,生日快乐。”**
而在南山的某个清晨,念念独自来到后山溪边,放下一只新折的纸船。船上画着三个小人,手牵着手,脚下延伸出密密麻麻的光线,织成一片星空。
她轻声说:“哥哥,我学会写故事了。下次讲给你听。”
纸船随水流远去,消失在晨雾之中。
同一时刻,全球十七个共频中心同步记录到一次短暂却强烈的信号波动。解码结果显示,仅有一个词:
**“好呀。”**
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疗愈中心的铭牌上。风吹动铜铃,叮当作响,如同回应。
世界依旧喧嚣,仍有太多孩子无法开口,太多父母仍在等待第一声“妈妈”。
但此刻,在某个看不见的维度里,有个男孩正牵着母亲的手,走在开满花的小路上。
他回头望了一眼人间,笑着说:
“别担心,我在听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