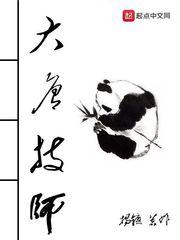笔趣阁>冲喜夫君一千岁 > 消散(第1页)
消散(第1页)
傅晚棠拄着桃木剑柄,剑尖深深陷入泥土,才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方才催动“列”字真言与“兵”字真言道力耗损过甚,喉头的腥甜才压下去。可望着满的狼藉,又看了眼昏迷的李平,想到遁走的附形邪魔,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又袭上心头。
她叹了口气,谋划良久,拼尽全力,终还是功亏一篑。
沈遇从灌木丛后跑出来,衣摆沾着草屑,声音由远及近略带着些急促:“小棠姑娘,你没事吧?”
傅晚棠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抬起左手,用袖子擦掉嘴角血迹,自己撑着剑柄咬着牙站了起来。她朝沈遇微微摇了摇头:“我没事,快看看李老丈。”
沈遇忙去查看李平,随后朝傅晚棠点了下头。傅晚棠松了口气,幸好李平无碍。
两人合力将李平抬上藏在义庄侧后的驴车,气氛沉闷。
“小棠姑娘……”沈遇看着傅晚棠惨白的脸色和嘴角未擦净的血迹出声道,“都怪我,竟未能察觉到那只黑猫潜近水位,让其坏了阵法,这才……”
“不关你事。”傅晚棠打断他,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沈遇能同自己一道过来,并担起激活五行阵的重任,在傅晚棠看来已非易事。她声音略带些疲惫:“是我一心想尽快诛灭邪魔,一时不察才……”她又摇了摇头,“现在说这些已无意义。”只得再想办法找到邪魔踪迹。
沈遇还想说什么,见她不愿多谈便把话咽了回去。但赶车时,他总偷偷瞅傅晚棠,欲言又止。
傅晚棠看了他一眼:“沈兄有话不妨直说。”
沈遇期期艾艾开口:“那个……小棠姑娘……你要不……先找点水漱漱口?”
傅晚棠不明所以。
沈遇又比划着做了个仰头喝东西又喷出的动作,脸上表情复杂,“你方才……这样那样……”
傅晚棠还是觉得莫名其妙:“何出此言?”她只是喝了一口雄黄酒而已,何需漱口。
“呃……”沈遇声音更低了,“沈某先前问过那包袱里……小棠姑娘不是说是从沈大老爷孙儿星星儿处取得的童子尿吗?小棠姑娘真是大义啊!为了对付邪魔,那……那童子尿说喝就喝!”沈遇一脸真诚,“小棠姑娘眼下定是难受得紧,赶紧漱漱口才好!”
傅晚棠脑袋懵了一下,她缓缓转过头,苍白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先是涨红,继而转青,然后一双杏眼睁得溜圆瞪着沈遇:“你!好你个沈遇!你瞎说什么呢!”她气恼,“我什么时候喝……童子尿了!”
沈遇被她瞪的结结巴巴:“沈某……沈某先前问时,小棠姑娘亲口说是童子尿……你方才不是拔开一个瓷瓶,然后……对着李老丈……”
“那是雄黄酒!驱邪用的!童子尿……在另一个瓶子里……我!没!喝!”最后三个字,她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脸颊依旧气得通红。
“啊?!哦哦!”沈遇彻底懵了,随即恍然大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是是是。沈某愚钝。误会,天大的误会!”他连连作揖告罪,再不敢抬头看傅晚棠,“雄黄酒好,雄黄酒甚好!驱邪圣物!小棠姑娘英明,英明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傅晚棠被沈遇这么一打岔,看他语无伦次的尴尬模样,将先前那股深深的挫败感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她仍没忘没好气地白了沈遇一眼。
紧赶慢赶,终于在城门关闭前一刻进了城。两人直接将李平送回了曲巷坊的家。李平之子与其妻王氏早已望眼欲穿。看到昏迷的李平被抬回来,吓得腿都软了。
“别慌。”傅晚棠安抚道,“李老丈已无碍,只是元气大伤,需要静养。我已去过医馆。”她递给王氏一个小瓷瓶,“这是大夫开的药丸,每日一粒,月余当可恢复。”李家人千恩万谢,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出了李家门,沈遇看向傅晚棠苍白的侧脸:“看小棠姑娘脸色,应尽快回去好生休息。”
傅晚棠点点头,可脚步却下意识又拐向了泥鳅巷的方向。沈遇无奈,只得默默跟上。
天色已暗,将破败的泥鳅巷笼罩在一片灰蓝之中。傅晚棠站在巷口,心情也如同这天色一般晦暗。虽李平得救,但邪魔未除,泥鳅巷游魂也就无法消散。她需得回去好好想想该如何追踪那遁入乱葬岗的邪魔。
然而,就在她驻足凝望之时,一阵风拂过面颊。
她为之一振,这风……不一样!
先前从巷子里吹出的风是阴冷透骨的“阴风”,而此刻拂过她面颊的风,虽然也带着深秋的凉意,却是清爽的带着泥土和枯草气息的“活风”!
傅晚棠眼睛一亮,立即冲入巷中。她掏出随身携带的罗盘,罗盘指针稳稳地指向北方,纹丝不动。
她难以置信,举着罗盘快步穿行在巷中。越往里走,心越跳得厉害。巷子还是老样子,泥泞破墙,整体昏沉,可那萦绕不散的阴郁之气真的没了!
暮色中的不过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深巷。
她又走近那堵倒塌的土墙下,目光瞥见空气似乎极其轻微地扭曲了一下,一个极其淡薄的灰白色虚影,缓缓浮现又在眨眼间彻底消散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