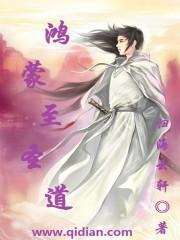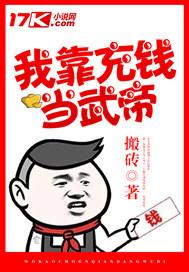笔趣阁>四合院:重生傻柱奖励超强体魄 > 第262章 全院大会易中海交锋棒梗(第2页)
第262章 全院大会易中海交锋棒梗(第2页)
老太太看着看着,忽然捂住嘴,眼泪掉了下来。
“我儿子小时候最爱画画,后来……吸毒被抓走了。我一直觉得,这楼里再不会有光了。”她哽咽着说,“可今天,我好像看见了。”
当天下午,在临时腾出的一间活动室里,何雨柱开了第一场“非正式分享会”。
没有PPT,没有麦克风,只有十几把椅子和一壶热茶。
他说起了自己重生前的日子:被人嘲笑“傻柱”,干活拼命却总被排挤,喜欢秦淮如十几年不敢开口,活得憋屈又窝囊。
“可当我醒来那天,身体变了,脑子也清楚了。我知道,这不是让我去报复谁,而是让我有机会重新做人??不只是为自己,也为这个院子。”
他讲到贾东旭如何从怀疑者变成共建者,讲到许大茂如何一笔一笔核对账目只为证明“我也能干干净净活一回”,讲到那位逃犯如今成了防汛组长,每逢暴雨夜必守在井盖旁。
“改变从来不是一声令下就发生的。”他说,“它是一顿饭、一次倾听、一句‘你试试看’积累起来的。你们这儿现在很难,但难不代表没希望。只要有人愿意迈出第一步,后面总会有人跟上来。”
散会后,李桂香找到他:“我想试试。我想建个值班表,每晚安排两个人巡楼,顺便看看哪家需要帮忙。电费咱们AA制,公开透明。你说行不行?”
“行。”何雨柱用力点头,“而且我可以帮你申请‘火种微基金’,首批支持十个老旧社区自治项目,你们符合全部条件。”
一个月后,筒子楼成立了首个“居民共治委员会”。楼道装上了感应灯,屋顶铺了第一批太阳能板,废弃的储藏室被改造成儿童自习角。而那个曾经充斥谩骂的微信群,如今每天早晨都会有一条消息准时发送:
【今日值班:李桂香+王建军|天气晴,宜晒被褥|爱心早餐已送达302刘奶奶家】
与此同时,四合院内部也在悄然升级。
“希望工坊”正式挂牌,成为全市首个社区技能认证中心。在这里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的年轻人,可以获得由市人社局备案的职业资格证书。课程涵盖家电维修、电路安装、心理疏导基础、老年陪护等多个实用方向。
张磊成了首席讲师。曾经只会撬锁的手,如今教孩子们如何安全接线、识别电压等级。他在黑板上写下第一句话:“技术无善恶,人心才是开关。”
陈浩则牵头组建了“家庭能源管家团”,为周边社区提供免费用电诊断服务。他们带着便携设备挨家挨户检测能耗漏洞,提出节能建议,甚至帮低收入家庭申请光伏补贴。
而许大茂,竟迷上了财务数据分析。他戴着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整理各社区上报的资金使用报表,发现某试点社区存在异常采购记录,及时上报后查实为个别干部虚报冒领,避免了十余万元损失。
市纪委专程致谢,并邀请他担任“基层廉政观察员”。
最让人意外的是,连那位曾逃亡三年的男人??孙有志,如今不仅负责防汛,还在公安部门支持下开设了“回归者互助小组”,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建生活。他的口头禅是:“我不是完人,但我正在变好。”
春天转入初夏,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袭击城市。
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内涝。地铁停运,道路积水,多个老旧小区地下室进水,居民被困。
火种应急指挥中心迅速启动。
何雨柱坐在议事厅主位,面前是八块实时监控屏,分别连接八个联盟社区。对讲机里传来各地声音:
“南城胡同积水达80厘米,老人行动不便,请支援!”
“西区汽配厂宿舍一楼全淹,急需抽水泵!”
“北园社区断电,药房冷藏药品危急!”
“收到。”何雨柱冷静下令,“一号车赶往南城,携带担架和防水毯;二号车调转方向,把泵先给西区;三号车保持待命,随时准备转移病患。太阳能应急站全部开启,优先保障医疗与通讯用电。”
秦淮如同步协调心理干预小组:“派出六支心理援助队,重点跟进独居老人和受灾儿童。记住,不要问‘你怕不怕’,要说‘我们在一起’。”
那一夜,风雨如磐。
四合院成了整个区域的中枢神经。青年帮全员出动,有的涉水背老人转移,有的在积水中排查漏电隐患;共育中心开放为临时安置点,提供热水、食物和充电服务;工坊里的焊工连夜改装了一批浮力救生担架。
孙有志带领防汛队彻夜值守,每隔半小时巡查一遍排水口,清掏堵塞杂物。当他浑身泥泞地从最后一个井口爬上来时,天已微亮。
雨停了。
城市伤痕累累,但八个联盟社区无一人伤亡,无一例重大财产损失瞒报。
媒体蜂拥而至。
记者问何雨柱:“你们凭什么做到这些?”
他指着身后忙碌的身影:“凭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退缩。我们没有超人,但我们有愿意扛事的人。”
数日后,《光明日报》整版报道《暴雨中的微光:一座四合院与它的火种网络》,引发全国关注。
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会议,将“火种模式”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典型案例库。民政部启动“万家灯火计划”,拟三年内在一万个城市社区推广类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