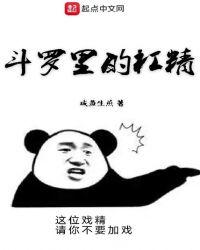笔趣阁>小病秧子养护指南 > 7080(第30页)
7080(第30页)
一本病历还剩最后两页。医生反复叮嘱,不要为了工作不要命。胃要养,要养。
千叮万嘱苦口婆心,谁知病患半句没听,开好的吊针留了三分之二。
到达别墅,家庭医生已等在门口。他说自己按过门铃,但家中好像没人。
盛恪按下密码,中午时分,别墅安安静静,没半点人气。
“走吧,人在楼上。”
打开房门,床上鼓着一团,那人抱着被子蜷得紧。
看似睡着,但高烧之人哪里能睡得好,何况傅渊逸还咳,咳又咳不出,全闷在肺里。
每次咳嗽前的吸气像极了漏了气的气球,气息在喉咙里打转,发出破败的声音,断断续续呛进肺里。
难受地紧闭双眼,肩膀随着剧烈的咳嗽不自觉地紧缩,又因肺里发紧难以呼吸而选择平躺。
咳嗽止息片刻,再次卷上来,傅渊逸压着无力咳嗽的肺,在床上痛苦地翻滚半圈,连带呼吸也愈发急促。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进门,直到忽然咳得停不下来,不得不半支起身体,才在模糊的视线里看到朝他而来的盛恪。
以为是自己不清醒。以前想念太盛的时候,幻觉常来,也总能见到盛恪。
抓着那人的衣袖,残破的呼吸一下下,硬是从泛着腥甜的喉咙压出一声,“哥,我好难受……”
声带仿佛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哑。
手里触及的皮肤烫得可以,盛恪替他拍着背,帮他咳过那一阵。
傅渊逸软下来,手还抓着盛恪,脖颈处涨得通红。睡衣第一颗扣子不知道何时松开的,衣领歪得不像话,露出半个肩头。
盛恪注意到在他锁骨上的疤,是以前不曾有的。
那疤不像是割破皮肉后留下的,没有凸起的增生瘢痕,而是一条暗红色的半弧形。
还没来得及收回神,傅渊逸突然挣扎着跪立起来。
盛恪扶住他,沉着脸色斥责,“傅渊逸,你又要……”
晃晃悠悠的人眼神迷离,张开手扑过来,抱住他的脖子,跌进他的怀里。发烫的眼睛、鼻息全都埋进他的颈侧,软着尾音一遍遍喊他,“盛恪……盛恪……盛恪……我难受,你都不管我……”
盛恪知他,再下去怕是就要哭了。
呼吸已经乱得一塌糊涂,再哭怕是得吸氧才能缓过,于是盛恪不客气地握着傅渊逸的后颈将他从身上撕下,警告道:“傅渊逸,再闹我走了。”
“不要。”傅渊逸抓着他,不太满意地吸着鼻子嘟嘟囔囔。
盛恪没管他在说什么,让一旁久等的家庭医生过来诊治。
第三人出现,还是陌生人,傅渊逸的眼睛瞪得大了些,眼瞳颤了又颤。
一双委屈发红的眼睛看看盛恪,看看家庭医生,再看看自己。等嘴里被盛恪塞了冰凉的温度计,才反应过来,“咳,哥,你是真的??”
盛恪冷脸皱眉,托着他的下巴让他闭嘴。
傅渊逸老实了,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地坐好量体温。量完体温,自己拉开衣服让家庭医生听诊。
“肺部以前有过什么问题吗?”家庭医生问。
“气胸、肺炎,还有过一段时间的轻度白肺。”回答的是盛恪。
“这几年有没有定期检查肺部情况?”
傅渊逸看着盛恪压根没听,等被盛恪凶了一眼,才摇头回答说“没”。
家庭医生再次听了一下傅渊逸的肺部,“肺部有些杂音和湿啰音。不过因为原本他肺部的情况就不太好,所以也不一定是炎症或者感染。”
他例行询问傅渊逸,“咳嗽有痰吗?”
“没有。”
“会感觉胸部压迫或是呼吸困难吗?”
傅渊逸还是摇头。盛恪又凶他,他挺无辜的缩着肩,“我平时也胸闷,呼吸比较浅,这都……正常的么……”
说完,他感觉他哥的脸色凶了不止三分,得有四五六七八分,后来他哥就不看他也不理他了。
早知道就不照实说了。傅渊逸用被子把脑袋也一起裹住,牙齿沿着下唇线咬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