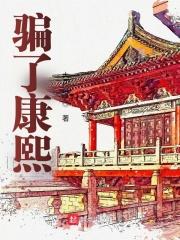笔趣阁>恶女抢了女主的白月光 > 怒其不争伤无忧(第3页)
怒其不争伤无忧(第3页)
池砚舟受不起他们的跪拜,把脚收回,他不解:“我受不起你们跪我,发生什么事了?”
王父连忙将家中发生的事告知,顺便提了一嘴马场也同王家一般被查封了,而管事于今早葬身马蹄下的事。
池砚舟心情复杂,晦暗不明看着他们:“我如何知晓是真是假,况且王泽佑也当知晓昨日我与崔大小姐不欢而散的事,这事我做不了主。”
王泽佑突然愤怒道:“她不是对你另眼相看吗?池砚舟你就是不想帮我。”
他平静瞧着王泽佑发疯,这事他确实帮不了。
池砚舟心知按崔扶钰的性子就算会报复王家,也不会拿人命不当事。
除非王家本身就做过不干净的事。
池砚舟忽然想起最近沸沸扬扬的私盐案和盐矿的事,他也不想蹚这趟浑水,“我这等小人能在崔大小姐面前值几个面子。”
话落,池砚舟直径去了他的位置上,不在理会王家,反复温习着前几日的功课。
王父心知无望叹息一声,自顾起身往外走。
王母连拉着王泽佑跟上。
——
彩色蝴蝶煽动翅膀从空中低飞,停留在玉棠院窗沿新换的鲜切荷花花上,嗅着幽香缓缓振动炫彩的翅膀。
崔扶钰一身粉衣,妆饰简单,周身神清气爽,笑容满满的出了院子,去往前厅与她爹娘共进早膳。
只是,她才到门口便听见里面传来她爹娘议论朝堂之事,她有心停在门口偷听,便让丫鬟们都噤声。
崔扶钰靠近门框,静静偷听。
崔仕海脸色凝重与赵缨说着今日早朝发生的事,盐矿一案已然查清楚了。
“今早汪飞身上还带着伤,就拿着他调查的结果呈给了圣人,圣人阅后大怒,折子都扔了,直接让羽林卫当场抓了四个共犯,唯有主犯张柴介还未抓到,汪飞大早带着人抄了好几家商户。”
赵缨小口喝着瑶柱肉丝粥,诧异听着:“这般严重,盐矿到底是大事,民生根本,可见张柴介接职务便利收敛了多少钱财,只是张柴介何故如此?”
按张柴介如今的位置至少保他衣食无忧,任谁都不会犯下这般大错。
赵缨唏嘘着张柴介的行事,他人至中年能做到京官盐运使这地位,可见他的才学。
只是一步行错,便回不了头。
“谁知呢,听圣人说他贪墨的钱财可顶国库五年营收,那张家抄家时也收刮不少越级财物,圣人有意让事化小,免动摇社稷,不过张家大抵是死罪难免了。”
崔仕海同样可惜感慨张柴介,同朝为官数十载,他与张柴介虽不熟,但也听过他的事迹。
若为官清廉,想来后续他能做出更大的政绩,万不该动了歪心思。
现如今的下场到是罪有应得了!
赵缨回想崔仕海说张柴介跑了,疑虑开口:“汪飞做事一向谨慎严谨,怎得就让他跑了,莫不是朝中有人和他通了气?”
张柴介跑了一事,太过巧合了。
崔仕海摇摇头,汪飞抄了张家时,张柴介已经不在家中,无人知其下落,怕是连夜跑的。
崔扶钰满意想:私盐和盐矿彻底解决就好,崔家便能多安稳一时。
同时,崔仕海凑近他夫人的身旁,神神叨叨:“你可知是谁让圣人突然去查盐矿吗?是咱们女儿拐弯抹角提醒我递折子!”
他说:“我这些天越想越不对劲,她怎么知道的?”
赵缨并没有回他的话,而且轻咳两下,提醒崔仕海,他口中料事如神的女儿已经来了。
崔仕海抬头露出笑容,瞧着他的乖女:“早啊,钰儿,昨夜睡得可好?”
一顿早餐吃得还算相安无事,崔扶钰也没在多问张柴介之事,她信执法司很快就会把他抓住。
谁想,崔扶钰回到玉棠院时,被人吓了一跳!
是暗轩的人回来了,女少侠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