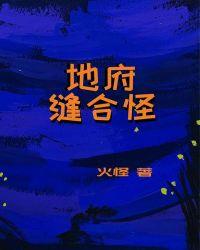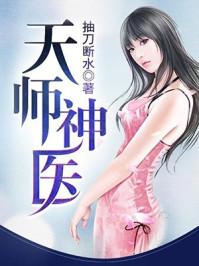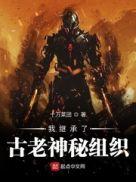笔趣阁>救!口嗨了装聋高岭之花 > 山雨欲来不如睡觉(第2页)
山雨欲来不如睡觉(第2页)
姜幼安无从得知,在她方才那番忐忑不安的陈词中,正对面的男人,目光一直落在被她抖出残影的银朱色短襦琵琶袖。
抑或说,是那一直在颤抖的银朱色短襦琵琶袖残影,硬生生地晃进他的眼中。
“不过,”岑回话锋一转,“我既已知此法,为何偏偏要找你呢?我手下能人异士,数不胜数。”
还沉浸在喜悦里的姜幼安一怔,这话好耳熟。
——我为何要替你解毒?
她不禁感慨,不愧是亲父子俩。
姜幼安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点她的不可替代性:“前期要行之事繁复无章,且尚且不知能否成事,小女愿承担一切后果。”
“不知能否成事……”岑回意味不明地温声重复她这句话,似在反复琢磨。
姜幼安忙道:“小女断然不敢拿毫不可行的法子来蒙骗大人。然而,小女也不敢断言此法十拿九稳。”
“是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事,由小女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做便好。”
“成不成,在小女一人而已,无关大人的事。”
“莫要紧张,”岑回和煦而言,“此事便交由你去做。若成,利国利民,我定重重有赏。”
“小女……小女,”姜幼安难为情地行礼,“仅、仅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岑回示意她免礼。
姜幼安瞥向岑霁,“事成,小女想向霁郎君,求——”她将琵琶袖攥成一个小球捏在手心,“一味药。”
她故意省却了“解”字。
“这有何不可,”岑回不仅应允了她,还道,“既然我儿正患此疾,你又意图了解通用的手势,不如就令他与你一同共行此事。”
他向岑霁望去,最不喜与人来往的儿子,在这番话后依旧泰然自若,像真未听见般惬意吃茶。
岑回如针在喉。
那年,他的嫡子岑霁自柳州舅父家归途,偶遇一场千载难逢的大雪,受寒惊神。
年仅四岁的他一朝喑聋,久治难医。
他这个作父亲的日夜心神难安,一为儿子日后行事生活,多有不便;二为幼时便才智尽显的儿子,就此断了官途。
如今有此法可试,他自然希望他的儿子能首当其冲习得。
内心深处,一些不能道明的猜忌,以及更多的不愿接受儿子当真喑哑的执念,被岑回一尽忽略了。
岑回的目光在姜幼安身上停驻一瞬,才将此事以及她求药一事,一同写与岑霁。
岑霁羽睫微眨,将一贯滴水不漏的父亲的多余一眼,分明看在眼里。
而姜幼安,小心翼翼瞥了眼一言未发的岑霁,又小心翼翼瞥了眼不由分说的岑回。
既希望岑霁答应,又不希望岑霁答应。
来自难以言说的直觉。
也许是太过顺利。
姜幼安在心中对自己的脑袋一顿暴击。
她真是被这群古代人pua了。
顺利还不好吗。
大抵是父命难违,岑霁答应了。但姜幼安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他多半是不情愿的。
因为岑霁看见“药”字时,目光极为淡漠,像要将那张薄薄的麻纸活生生看出个洞来。
主院离岑霁的虚明院以及姜幼安的偏院皆有段距离,前者坐四条腿的马车,而后者靠两条腿的人车。
岑回体贴地令他们二人一同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