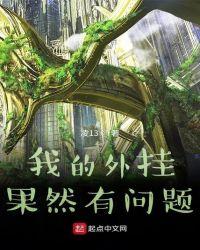笔趣阁>重燃青葱时代李珞应禅溪免费无错版 > 第877章 辩经(第3页)
第877章 辩经(第3页)
它破土之前,也在黑暗里挣扎了很久。
但它终究会长出来,因为大地记得它的根。”
当天下午,他们联系社区档案室,查到林小树的母亲三年前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父亲拒绝探视,孩子便一直被托付给年迈的外婆,老人去世后,他只能勉强维持上学与生存之间的平衡。
袁婉青决定启动“一对一通信计划”
。
她在志愿者名单中挑选了一位特殊导师??周老师。
这位曾烧掉情书草稿的退休语文教师,如今已是“盲信漂流”
的核心通信员,每月坚持手写回信给十名困境儿童。
当周老师读完林小树的信,沉默良久,提笔写下第一封回信:
>“亲爱的小树:
>我七岁那年,也被邻居小孩指着鼻子说‘你妈疯了,你是没人要的’。
我回家问奶奶,她抱着我说:‘他们不懂,真正的家人,是哪怕世界抛弃你,仍愿意为你留一盏灯的人。
’
>你现在觉得冷,是因为你正站在风里。
但请相信,总有人会为你挡一阵风,哪怕只是片刻。”
信寄出第三天,林小树出现在邮局门口。
这次他带来了整整一本练习册,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未寄出的信。
有一封写给母亲:“我想你煮的鸡蛋羹,软软的,不烫嘴。
护士阿姨说你快好了,我能去看你吗?”
有一封写给父亲:“如果你真的不要我,能不能至少告诉我妈妈在哪?我不恨你,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
最后一封,日期是昨夜:
>“今天有个老爷爷给我回信了。
他不认识我,却说我不是孤单的。
我把信贴在胸口,听到了心跳。
原来我还活着,而且有人在乎。”
袁婉青将这些信扫描归档,同时申请心理干预绿色通道。
一周后,林小树的母亲被转至康复期疗养院,医生评估认为可以尝试亲情重建。
见面那天,袁婉青陪他走进病房。
女人瘦削苍白,眼神起初涣散,直到看见儿子手中紧握的那本练习册。
“这是……小树写的?”
她颤抖着翻开,泪水瞬间滑落,“他记得我喜欢加一点点糖……他还记得……”
母子相拥而泣。
袁婉青悄悄退出房间,靠在走廊墙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手机震动,是王小舟的消息:【姐,苏念画了一幅新画,说要送给所有帮过小树的人。
】附图是一棵大树,枝干由无数信纸缠绕而成,树叶是各种颜色的心形,树根深入地下,连接着一个个小小的名字:田穗、林小满、林小树……
她还没来得及回复,陈默发来一条语音:“我在青海的学生来了电话。
他说今年高考志愿填了心理学。
‘我要成为那个肯听我说话的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