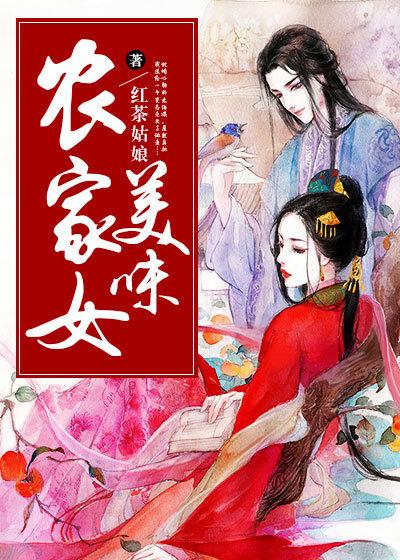笔趣阁>续春 > 第450章(第1页)
第450章(第1页)
“太妃!”崔老夫人自是不肯这么轻易作罢,“绣使此等行径,不仅是羞辱我镇国公府满门忠烈,更是亵渎先圣亲赐的勋爵体面!先圣若在天有灵,见此折辱功臣遗属之举,岂能瞑目?!恳请太妃娘娘秉持公道!”
“崔老夫人好一张利嘴啊——”颜如玉勾着唇带着几分讥诮,“听闻老夫人当街咒骂本使,说什么‘穿绣衣的狗’,又说‘主子是卖屁股得的权势’,不知老夫人所说的‘狗’指的是谁?本使何时卖了屁股,谁又买了本使的屁股?此等污言秽语羞辱朝廷命官,是国公府的体面,还是先圣的体面?”
殿内空气仿佛冻结。
“颜如玉,你放肆了!”太妃猛地一拍扶手,霍然起身,声音陡然拔高,带着装腔作势的雷霆之怒,“哀家面前,岂容你如此无状!国公夫人因担忧儿子病重而悲痛失言,你自当体谅!你身为朝廷重臣,不思己过,竟敢在哀家面前反唇相讥,质问勋贵?!谁给你的胆子!”
颜如玉垂首,不再辩解:“臣,知罪。”
太妃深吸一口气,仿佛强压怒火:“传哀家懿旨!绣衣直使指挥使颜如玉,行事狂悖,着即罚俸一年!于府中面壁思过三日,深刻反省!”
“三日?三日怎——”崔老夫人不服,脸上的褶子挤得愈发深了,再欲说些什么,却被镇国公用眼神制止。
“臣……谢太妃娘娘恩典。”颜如玉叩首,声音依旧听不出波澜。他起身,目不斜视地退出大殿,将镇国公夫妇那混杂着不甘与一丝得逞的目光甩在身后。
宫门外,冰冷的空气涌入肺腑。颜如玉刚走下台阶,知树的身影如同影子般无声靠近,声音压得极低,带着紧迫:
“公子,刚刚得到的消息,莫星河定了日子,三日后子时,对钟离政下手!”
富贵的马车
崔老夫人从宫里出来,冲着镇国公抱怨:“你怎么不让我多说几句?三日顶什么用?你我入宫是为了什么,就为了看他俩唱着一出双簧戏?”
不等镇国公开口,崔老夫人又道:“吕芳这个寡妇当真是没有半点廉耻了,养出那么一条狗来,还公然偏袒。”
镇国公揽着胡须气喘吁吁地爬上马车,坐定之后才说:“平日你最是得体,怎的这几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说人‘卖屁股’,吕芳听了没翻脸,还能给你几句场面话已是顾及镇国公府的脸面了。”
“我那日也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崔老夫人正欲辩解。
“我知道,”镇国公抬起手摆了摆,示意她不用多说,他抚着胡须想了又想,“那个丫头真是什么药引子?这事我总觉得有些邪乎。如今朝中局势诡谲,京城又总有女娃娃失踪,还是要慎重一些才好。”
崔老夫人听得这话,很是不屑。
堂堂国公府若如此谨小慎微,那还做什么国公?权贵就要有权贵的优待。人牙子卖的奴仆又有多少不是拐来的?再说,又不是要做多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过是拿一个小姑娘来用一用,国公府愿意用她,已是天大的福报了。
崔老夫人说:“我已想好了,等老二病一好,就让他把那姑娘给收作通房。”
“嗯,这倒是不错,也不算亏待人家。”镇国公赞许地点点头,“家中的事,你向来操持得妥帖。”
崔老夫人心头又舒坦了一些,眉间的川字纹舒展开了。为了入宫,起得太早,马车晃晃悠悠,让她有些昏昏欲睡,最后干脆靠着车壁闭眼假寐。
忽地马儿响起一声嘶鸣,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