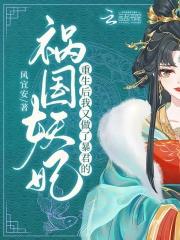笔趣阁>岁时食肆[美食] > 天穿篇 补天穿(第1页)
天穿篇 补天穿(第1页)
正月二十,是为天穿节。
李渔说,最早记载天穿节的资料是东晋王嘉所撰《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曰补天穿。
天穿节与女娲补天的神话相关,传说女娲在正月二十日炼五色石补天,拯救苍生。人们在这一天纪念女娲,祈求风调雨顺、家宅平安。
瑶掌柜等人忙着做煎饼、祭祀女娲娘娘。姜糖没有参与,她回到岁时食肆已有数日,魂儿却好像丢了一半在天宝三载的长安。
驱岁煞、接灶神、斗姑获、猜人心、乃至直面春神句芒的威压,都不及幻境中那一个月的相依为命来得刻骨铭心。
那个有着胡人深邃眼廓却又在长安受尽冷暖的小孩,他那份与年龄不符的倔强和依赖,扎在姜糖心尖上,持续不断地散发着隐痛。
除此之外,姜糖还不得不忍受着另一种来自神魂深处的疼痛,大概是再次使用司历尺留下的后遗症,时刻都提醒着她那场未完成的灌顶。
思来想去,她忍不住开始翻遍食肆藏书阁里所有与司历一脉相关的典籍玉简、竹简、帛书,除却某些前辈大能留下的神识烙印她看不了,其它的她都一一检视,寻找张雪樵三个字。
“《司历谱·唐·张雪樵》……‘渡淮阳饿殍,活人无算’……‘性孤洁,术法精绝’……‘后踪渺,疑登仙’……”
记载寥寥,语焉不详。这位惊才绝艳的前辈,如同投入岁月长河的一颗石子,漾开几圈涟漪后便再无踪迹。
姜糖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在那个上元节,遇到一个名叫二狗的小孩?她甚至抱着一丝荒谬的期望,希望能从这些冰冷的文字里,找到二狗后来去向的蛛丝马迹。
自然是徒劳。
她合上最后一卷兽皮册,尘埃在从雕花木窗棂透入的光柱中飞舞。
姜糖叹了口气,把脸埋进臂弯里。明知不可能,却还是忍不住去寻找,这种徒劳的执着,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小姜丫头,晌午了,怎地还窝在此处?今日蜜娘新试了玉露团,去晚了可就被阿赤抢光了!”
李渔的声音带着戏谑从门口传来。老先生今日换了身簇新的靛蓝道袍,银白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苟,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如果忽略他胡子上的糖霜的话。
姜糖迅速抬起头,扯出一个笑:“就来!师父,您胡子上沾了蜜。”
李渔“哎呀”一声,忙不迭地用袖子去擦,嘴里嘟囔着:“定是方才帮蜜娘试味时不小心……”他的目光在姜糖脸上转了一圈,嘿嘿笑道:“小丫头,学会转移话题了。可是在寻什么?或是在找什么人?”
姜糖心里一紧,下意识回避:“没有,就是看看前辈们的事迹,激励自己。”
她不想说。倒不是不信任李渔,只是这经历说起来并不精彩,无非是一个现代大学毕业生在古代幻境里带了一个月孩子,最后还失败了。
更何况,李渔这促狭的性子,若知道她为个小孩子茶饭不思,还不知要怎么打趣她。
“是吗?”李渔挑眉,显然不信,但见她不愿多谈,也不再逼问,只摇摇头,“年轻人,心事比老夫的褶子还多。快些来,美食当前,愁肠也得给饥肠让位。”
食肆大堂里,果然香气扑鼻。
胡蜜娘端着一盘晶莹剔透、形如荷花绽放的糕点走来,见到姜糖,嫣然一笑:“小祖宗快来,这玉露团用了新熬的蜜浆,拌了剁碎的苹果和酥酪,清甜不腻,最合这时节吃。”
阿赤已经抱着个空盘子,正眼巴巴地看着新出炉的点心。
姜糖被他们逗得暂时忘了心事,拿起一块玉露团咬了一口,清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的确美味。但她吃了小半个,便放下了。
这举动没逃过瑶掌柜的眼睛。
傍晚,姜糖独自坐在食肆后院的石阶上,看着天际最后一抹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