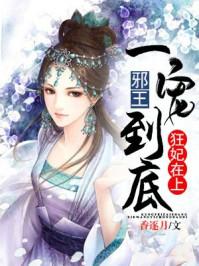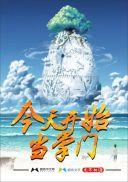笔趣阁>说好艺考当明星,你搞神话战魂? > 第68章 登顶江一鸣晋升二线超凡明星(第3页)
第68章 登顶江一鸣晋升二线超凡明星(第3页)
会议室陷入死寂。
良久,主座上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那就让他们响吧。反正……声音再大,也吵不醒装睡的人。”
话音未落,天花板忽地传来细微响动。
叮??
一声清脆的铃音,轻轻落下。
所有人抬头望去。
通风管道口,不知何时挂上了一只小巧的铜铃,正随空调气流微微摆动。
它本不该存在。
更不该响。
可就在那一瞬,每个人都听到了??
一段口琴声,从铃中渗出,缓慢、沙哑,带着金属摩擦般的粗粝感,像风刮过废墟,像雨打在铁皮屋顶。
正是《默语》的开头。
有人猛地站起,伸手要去摘铃。
“别碰!”技术主管嘶吼,“它可能是触发装置!一旦物理接触,可能会激活更大规模的远程共鸣!”
那人僵在原地。
铃音持续了整整五分钟,然后戛然而止。
室内恢复寂静。
但每个人的耳膜深处,似乎仍有余震未平。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悄然发生着变化:
-柏林一家美术馆展出一组“会唱歌的雕塑”,参观者靠近时,耳边便会响起陌生人的低语告白;
-东京地铁站的广告屏深夜自动切换画面,播放一段无伴奏合唱,歌词是中文:“我不是机器,我也会疼”;
-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下方被人嵌入微型扬声器,只要有人坐下超过十分钟,就会听到一句温柔的女声:“你想家了吗?”
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
但每一个接收者,都在社交平台上留下同一句话:
**“我听见了。”**
而在云南深山的某个清晨,苏瑶踩着露水走进一座新改建的“回声驿站”??这次是用废弃的铁路信号站改造而成。她打开录音机,放入一盘从芒岗寄来的磁带。
按下播放键。
没有语言,没有旋律,只有一阵风吹过群铃的声响。
但她听懂了。
她含着泪,对着麦克风轻声回应:
“我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