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说好艺考当明星,你搞神话战魂? > 第73章 南影北视的争抢(第3页)
第73章 南影北视的争抢(第3页)
上海某写字楼顶层,一家科技公司宣布关闭所有员工情绪监测系统,并公开销毁十年来积累的心理数据。“我们不需要完美的效率机器,”CEO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要的是会累、会难过、也会为一朵晚霞感动的真实人类。”
成都街头,一群年轻人发起“噪音日”活动,鼓励市民在特定时段大声喊叫、唱歌、敲锅打盆。警方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派出巡逻车播放民间小调助兴。
而在西北某偏远小镇的疗养院内,陆昭坐在轮椅上,面向窗外。他瘦了许多,眼神却不再冰冷。床头柜上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里面反复播放着一段模糊的音频??那是从雄安废弃公园偷录的合奏片段。
护士说,他已经连续听了七天。
昨天夜里,他突然坐起来,拿起纸笔,一笔一画写下了一首歌的简谱。没有人知道名字,也没有人听他解释。但他写完后,嘴角第一次扬起了真正的笑意。
---
一个月后,林默与苏瑶踏上新的旅程。
他们没有宣布目的地,也没有通知媒体。一辆改装过的厢式货车载着几十件手工乐器、数百枚记忆陶片、以及一套便携式声波测绘设备,驶向西南边陲。
沿途,他们在一个个小镇停留。每到一处,便召集当地人分享故事,收集声音,埋设“回响锚点”。这些锚点并不显眼:可能是祠堂梁柱里嵌入的一块共振木,可能是古井石栏下埋藏的青铜片,也可能是一口挂在村口的老钟内部涂覆的特殊釉料。
它们静静等待,直到某个特定频率唤醒沉睡的记忆。
有人质疑他们是在搞“情感煽动”,甚至有地方政府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试图阻拦。但每当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往往会被正在进行的集体吟唱所感染。有人想起童年走失时陌生人递来的糖果,有人记起高考落榜那晚父亲默默放在桌上的热汤面……最终,多数人都选择默默离开,或干脆脱下制服,加入其中。
半年后,全国已有超过一千个村庄建立起自主运行的“声音共同体”。它们互不隶属,却通过共享的声学密码悄然相连。每逢月圆之夜,某些村庄会自发同步举行“共鸣仪式”,虽相隔千里,却仿佛同奏一曲。
科学家称之为“跨地域群体记忆共振现象”;诗人称其为“大地的心跳重新接上了脉搏”;而孩子们只是笑着说:“因为我们都在听同一个故事啊。”
---
又是一年清明。
这一次,林默站在贵州山区一所小学的操场上。台下坐着上百名学生,最小的六岁,最大的不过十四。他们大多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儿童或残障群体,许多人从未走出过大山。
林默举起一支全新的竹笛。
“今天,我不教你们怎么吹出标准音阶。”他说,“我要教你们一件事??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就对着风吹一口气。不用用力,也不用完美。只要让它出去就好。”
孩子们睁大眼睛。
“因为总有一天,somewherefaraway,会有另一个人,也在对着风说话。你们的声音会在空中相遇,交织成一首无人听过的歌。”
他将笛子递出去。
第一个接过的是个聋哑女孩。她不会吹,但她把笛子贴在胸口,用手轻轻拍打,模拟心跳的节奏。第二个男孩则把它当成笔,在纸上画出他认为“风的声音”是什么形状。
林默看着他们,笑了。
他知道,这场战争早已超越胜负。
它不再是对抗某个组织、某项技术、某种理念。
它是对遗忘本身的宣战。
是向所有曾被迫沉默的生命宣告:你们的存在,值得被听见。
哪怕只有一个音符,也能撕裂万籁俱寂的长夜。
太阳升起,照亮群山。
山谷间,传来第一声稚嫩的笛响。
不成调,却无比清晰。
像春天破土的第一株嫩芽。
像黑暗尽头,那一道不肯熄灭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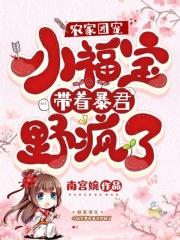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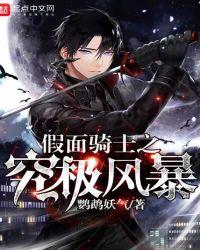
![专治极品[快穿]](/img/306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