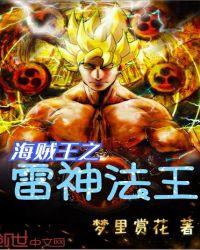笔趣阁>葬明1644 > 第211章 刮地皮(第2页)
第211章 刮地皮(第2页)
这老小子一开始,还东食西宿,想要两头兼顾,但是很快,伴随着襄樊营的急速扩张,行情一路上涨,尤其是去岁的秋季战事之后,张维桢如愿以偿的当上参事室总参事,他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的放在了襄樊营事务上。
杨士科彻底成为了牛夫人。
不过好在如今中军衙门职权扩张,县衙里也没那么多事情了,杨士科这个县令,变成了纯粹的庶务官。且由于襄樊营如今在乡下大搞屯堡,而屯堡系统又不归县衙管,杨士科能忙的事情就更少了。
当然了,杨士科自己可能未必觉得这是好事。
“老夫也并非为那刘明远说话,只是大人原先很是注重与地方上的官绅往来,很注重,呃。。。。。。这个影响。今日却见大人将一众南阳官绅晾在一旁,是以觉得大人莫非是另有深意?”
“谈不上深意。”韩复看着前方,淡淡说道:“本官在鲁阳关与鞑子厮杀之时,南阳官绅传言四起,恨我韩再兴不早死。这个时候,合该晾一晾他们。不仅这些人要晾,本官还要让魏大胡子,领着人头阵,去城中武装游行一
番,让全城一起震一震!”
南阳四面空旷,无险可守。真实的历史上,李自成退出河南以后,南阳等处的州县全都投降了清廷。虽然是无奈之举,但韩复从心里来说,对这些人也没什么好感。
而且,张维桢和张全忠这哼哈二将,过去半个月,一个敲诈官府,一个勒索士绅,把南阳城搞得鸡飞狗跳,将全城的官绅几乎都得罪完了。
对于韩复来说,这个地方也没有了统战和拉拢的价值。
他打算至多在南阳城外的卧龙岗停留一两天,然后全军撤回襄阳,也没必要再费心思,维护与南阳官绅们的关系。
之所以还要让魏大胡子他们进城游行,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为襄樊营打广告。
往后明清双方的主战场是长江流域,清廷在河南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韩复将自己抗清名将的形象树立起来,等于就是一面旗帜,将来河南要是有反清义军什么的,也好有一个投奔的目标。
而至于刘苏、吴这些具体的官僚,对于韩复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
牛万才倒是值得拉拢,但在李自成没死之前,韩复想拉也拉不过来啊。
襄樊营大军唱着军歌,浩浩荡荡,绕过南阳城,来到了南郊的卧龙岗。
韩复北上之前,特地调叶崇训率新勇营,赵守财率火器营,赵石斛率水营驻扎在南阳左近,一来作为接应,二来则以武力作为震慑,保障二张刮地皮的差事。
这时,叶崇训、赵守财,赵石斛和张全忠、韩文等人,早已在山门前等候。
见了面,一番吹吹捧捧之后,又来到了武侯祠。
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之后,韩复把张维桢和张全忠这两个人留了下来。
张全忠穿了件上好的松江棉布道袍,颌下一部美髯打理的洁净整齐,看起来很有几分人模狗样,仙风道骨的感觉。
“大人。”张全忠拱了拱手,脸露喜色的汇报起了他在南阳的战果:“大人北上之后,贫道照着大人所说,在城中发动士绅,搞助饷抗清之运动。起初,很有几家大户想不通,有抵触情绪。贫道只得带着军爷上门去,挨家挨户
的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算是让他们认识到了,何谓民族大义,何谓保家卫国。”
张全忠作为襄樊营的总宣教官,整日随侍韩复左右,受韩科长的“语言污染”最为严重,现在言谈举止,都很有“官气”。
这老道这些日子在南阳吃香喝辣,威风八面,战果很是喜人。
此时摇头晃脑,得意洋洋。
据张全忠所说,南阳城中,包括城关镇和近一带,共有大户37家。他按照田亩、家资、营生、官职等标准,给各家都摊派了一定数额的粮饷。
由于韩复告诉张全忠,南阳这个地方守不住,城里的粮食和银子与其将来留给鞑子用,不如咱们襄樊营弄过来自己用。不过尽管张全忠是抱着捞最后一笔的想法,摊派的比较狠,可城中大户也确实没多少油水。
37家大户,共计捐银二万七千四百两,粮食八千两百石,平均一家摊派了银740两,粮200余石。
和较为富庶的襄阳府肯定没法比,主要是南阳的大户,早就跑了一大半,剩下的这些歪瓜裂枣,自然就差了点意思。
不过韩复本来就是有枣枣打两竿子,能够弄到这么多粮饷,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至于风评什么的,他已经毫不在意了。
还是那句话,只要襄樊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自有大儒为我辩经。
我大清搞圈地投充,搞剃发易服,杀得神州人头滚滚,都能被洗成新朝雅政。他这点小手段,简直就是洒洒水,不值一提。
而且,一旦战事进入相持阶段,清军是要以南阳作为基地,来攻打襄阳的,南阳的这些物资,自己不搜刮,鞑子也会搜刮,韩复可不会为了什么虚名,而做留下粮食资敌的蠢事。
除了粮饷之外,张全忠还弄到了骡马58匹,以及一些房契、地契、字画古董什么的。
这些东西韩复不太感兴趣,尤其是古董。以他的眼光来看,这年头的任何东西都是古董,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