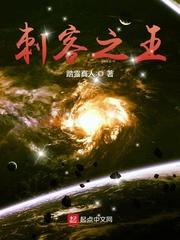笔趣阁>万人嫌重生后后悔了 > 6070(第10页)
6070(第10页)
目光扫了一眼,凝视着那辆不起眼的黑色红旗。
每天都来,来了就朝楼下旁隐蔽的街道一藏,朝九晚五,准时准点,跟上班来了似的!
又上不来,也见不到他,不知道有什么好坚持的。
何金玉甩手拉上帘子,走到办公桌坐下。
小桃开门进来,“何总,先生和夫人说要和您一起吃顿饭,就在今晚。”
他翻看报表,“我晚上还要开会,再说吧。”
“……”
他掀起眼皮,小桃没走,一脸怪异地看着他。
“怎么了?”
“那个,是周夫人啊,周夫人和周先生要答谢那天医院的事,所以在今晚也邀请了您,哈哈。”
“是吗?”
“对呀。”
何金玉托腮,一脸愁容,“我什么时候这么受欢迎了。”
一下来了两场来自长辈的饭局邀约,跟曾经的狐朋狗友叫去喝酒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也算是对他人品的认可了。
人品的认可。这几个字他听了都忍不住想笑。
而小桃思考了一下,当即出了个主意:“要不抓两个不老实的您当街打一顿吧,这样传出去,他们就不敢再靠近您了!”
“……”
何金玉沉默了一会,由衷道:“你以后少跟小理玩。”-
没下过雪的深冬没那么凛冽,冰冰凉的微风浸润在散着寒气的发梢与眼底。周霆琛抵着红旗车门,身穿冷黑的呢子大衣,身段颀长笔直,宛若雪地里挺拔的松柏。
市局门口,宝相庄严的警徽淬着雪白的亮光。
郎庄脸色森寒地出来,看到门口孤零零的一辆黑车,表情立马跟吃了狗屎一样。
“终于出来了,里面的滋味如何?”周霆琛冲他挑眉,大有一副胜利者的挑衅。
郎庄咬牙,“你以为,扳倒了我你就赢了吗?你——”
“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喜欢何金玉吗?”周霆琛没有跟他在某些没必要的方面费口舌,于是直接打断了他,道:“我和他一直都知道你会对我们下手,因为上一世你就是这么干的,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看着郎庄的脸色由不可置信转成惊惶再一点一点冷却,心里没有一丝大仇得报的欣喜,反而脸色更加冷冽:“你伤他的心伤了两次,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了。其实就算没有这些事情,他也不会喜欢你,郎庄,你什么都给不了他,何必做这些徒劳的挣扎呢,醒醒吧。”
郎庄的眼神完全变了,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归国不久、家道中落的18岁的周霆琛,而是一个全新未知、陌生疏离的面孔。
郎庄瞪着他:“难怪啊。”
周霆琛起身,皮鞋踩着地砖,一步一步慢慢逼近。
“你前不久去相亲了,听说双方都很满意,你会结婚吗?如果不会,那未来也打算不结婚?听说你们郎家世代单传,你父亲会允许香火断在你这里?郎庄,你不敢违抗你父亲,甚至不敢离开郎家,你明明什么都做不到凭什么不允许何金玉爱别人?”
“爱别人?”
郎庄品着这三个字,俊朗的五官立刻扭曲,体内蛰伏的暴虐因子也随着沸腾的怒火而暴起。不管他将自己伪装的多好,每每碰上何金玉,完美的面具总会被撕得粉碎。
就像现在,他已经不管还在警局门口,抵着周霆琛把人朝车门狠撞,“不准再说这种话了!他先认识的人是我!他为什么要爱别人,除了我,谁也不配得到他的爱!你少在这夸大其词,结个婚而已,等我全权掌控了郎家大不了离婚就是,什么香火,什么狗屁单传我都不在乎!我为了金玉什么都可以做,也什么都能做到!他爱谁不一样,你以为你在他心里是什么很重要的角色吗?”
周霆琛被他抵在玻璃上,澄澈乌黑的眼底倒映着男人暴走的撕裂表情。
淡道:“假设何金玉也喜欢你,他看到你跟别的女人结婚心里会怎么想?”
站在何金玉的角度去思考,那个时候他是会伤心还是继续喜欢?会不会难过的在深夜流泪?如果他真的在为此伤悲,那要如何做才能哄好他?
这些全是郎庄从来没想过的。
他眼底闪过茫然。
周霆琛嗤笑,“如果真有那天,何金玉一定会先拿刀砍了你,他那样骄傲的人怎么会允许另一半不全心全意对他呢?所以我说让你醒醒,你这么自私,跟他永远不可能。”
他抓着郎庄紫红的拳头,硬生生从身上掰下来,“你的‘什么都可以做’其实是不折手段折磨何金玉罢了,你所谓的付出都只是为了一己私欲,满足你那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不一样,我敢保证我这辈子不结婚;敢净身离开周家;敢永远不伤害何金玉,我会爱他、呵护他一辈子!”
他抓着手腕的指骨几乎要攥断骨头似的,抬手推开!郎庄体力透支,羸弱的病体趔趄几步跌坐在地,他睚眦欲裂地瞪着周霆琛,可喉间仿佛被什么东西钉住了似的,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