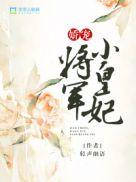笔趣阁>我要当大官 > 第二百二十四章 东阳盛景 天下大势(第1页)
第二百二十四章 东阳盛景 天下大势(第1页)
两艘船为了争抢繁忙的渡口停靠而撞在了一起,双方就此打将起来。
扭打不过片刻,就有军警吹着哨子跑来,一顿杀威棒打下去,将两边人揍得抱头蹲地,很快“埠头”赶来评定责任,制定赔偿,并进行罚款。
。。。
风从塔什布拉克村的东头刮到西头,卷起细沙,在阳光下闪出金粉般的光。李燕坐在“声音小屋”的屋檐下,膝上摊着那张孩子唱过的纸条,字迹已被风吹得微微卷边。他没有动笔修改,只是反复默念那两句歌词,像在听一段尚未完成的祷告。
木匠老阿迪力走过来,手里拎着一截雕好的横梁,上面刻着一行东干族民谣:“黄土埋人不埋心,歌子传下来就是命。”他把横梁比在门框上,点点头:“差两寸,还得刨一刨。”
李燕抬头问:“您小时候谁教您唱歌?”
老阿迪力愣了一下,咧嘴笑了:“我妈。她烧火做饭时总哼,说不唱就忘了日子是甜是苦。”顿了顿,又低声补了一句,“她走那年,我才发现,我已经不会唱她最后唱的那首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进李燕的心里。他忽然想起陈守义交出手抄本时的眼神??不是交付文物的庄重,而是托孤般的疲惫与希望交织。那些名字、那些歌、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原本不该由一台机器或一个项目来承接。可现实是,愿意听的人越来越少,能唱的人越来越老,而时间,从不等人。
入夜后,村里通了临时电。发电机嗡嗡作响,“声音小屋”内亮起一圈暖黄色的灯带。苏婉远程连线调试系统,屏幕上的波形图随着村民试音起伏跳动。“信噪比达标,环境共振捕捉效率提升40%。”她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冷静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我们终于建成了第一个真正属于村民自己的记忆空间。”
当晚,村里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录音仪式。七位老人围坐一圈,盲妇被安排在正中。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艾德莱斯绸裙,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仿佛等待登台的主角。主持人是村小学的语文老师,普通话略带口音,却格外真诚:“今天我们不录历史,也不录英雄。我们就录??谁最想让以后的人听见。”
第一位站起来的是村医吐尔逊娜依,五十多岁,一辈子守着这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村。她说:“我想让我孙女知道,2008年雪灾那个月,我背着药箱走了四天三夜,救活了六个难产的孕妇。我不是医生,可那时候,没人能不来找我。”
她说话时语气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但当录音结束,她摘下耳机,眼眶已经红了。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轻。”她喃喃道,“可做的事一点都不轻。”
接着是一位退伍老兵,曾参加过边境巡逻。他没说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讲了一件小事:有一年除夕,暴风雪封山,连队断粮三天。指导员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掰成七小块,每人一口。大家含在嘴里舍不得嚼,就为了尝个味道。“那天晚上,我们七个男人抱在一起哭,不是因为饿,是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还在一起,就不是真的冷。”
轮到盲妇时,全场安静下来。她没拿稿子,也没人搀扶,自己缓缓站起,朝着声音采集器的方向微微颔首,然后开口??依旧是那段《乌古孜传》,但她唱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慢,每一个音节都像从肺腑深处挤出来,带着岁月的重量和灵魂的震颤。
唱到中途,她突然停顿,轻声说:“老头子,今天有人在听呢。你听见了吗?咱们的名字,说不定也能留在风里了。”
那一刻,屋里没有人说话。几个年轻人低头抹泪,连一向调皮的孩子们都屏住了呼吸。李燕站在角落,看着监测屏上那条剧烈波动的情感曲线,忽然意识到:这不是技术的成功,是人性的共鸣。AI可以分析语调、还原语音、匹配情绪,但它无法创造这种瞬间??一个人用尽一生沉默后,终于敢说出“我也曾重要”。
第二天清晨,李燕独自爬上村子背后的沙丘。这里视野开阔,能望见远处雪山的轮廓。他打开录音笔,对着朝阳按下录制键。
“今天是‘声音小屋’启用第二天。昨晚那个老兵说‘只要还在一起,就不是真的冷’。我在想,也许人类最深的恐惧,从来不是死亡,而是被彻底遗忘??连存在过的痕迹都被抹去。”
他顿了顿,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但我们正在做的,或许就是在对抗这种遗忘。不是靠纪念碑,也不是靠史书,而是靠一句歌、一段话、一声叹息。它们微弱,但真实;短暂,却可能永恒。因为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记忆就不会断流。”
回到营地时,发现邓伦发来一条消息:“青海那位傈僳族妈妈昨天带着女儿来记忆驿站了。她们一起录了《摇篮曲》的对唱版。女儿说:‘我现在懂了,妈妈小时候也是被这样哄睡的。’”
李燕看着这条消息,久久未回。他知道,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正在悄然改变某种东西。不是政策,不是体制,而是人心之间的距离。从前,祖辈的故事被视为“陈年旧事”,年轻人觉得无趣;如今,一首歌能让两代人相拥而泣。这不是怀旧,是连接。
一周后,第一批“家音课”优秀作品评选结果公布。藏族小女孩讲述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入选全国十佳,教育部专门发函表扬,并邀请她赴京参加青少年文化论坛。消息传来那天,全村放了鞭炮,村委会门口挂起了横幅:“我们也曾温暖过世界”。
李燕陪女孩一家前往北京。途中转机时,她在机场书店看见一本关于进藏公路修建史的书,指着其中一张模糊照片说:“这个背影,有点像信里那个叔叔。”
随行记者拍下了这一幕。照片后来登上多家媒体头条,标题写着:《一百年前的光,照进了她的春天》。
论坛当天,小女孩站在台上,声音不大,但清晰坚定:“老师让我们写感受,我就写了三个字:他也暖。因为我阿妈说,救人的人,心里一定也很冷。可他还是伸出了手。所以我觉得,暖不只是温度,是选择。”
台下掌声如潮。一位退休历史教授站起来提问:“小朋友,你觉得几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你说的这个故事吗?”
女孩想了想,摇头:“我不知道。但我奶奶说,只要我还记得,它就没消失。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会讲给他听。”
李燕坐在后排,眼眶发热。他知道,这正是“忆”项目的终极意义??不追求永生,只求延续;不要宏大叙事,只要真心传递。当一个普通人愿意把另一普通人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文明便完成了它最朴素的传承。
返程途中,苏婉来电:“模型又有突破。我们现在可以用极低数据量复原残损录音中的情感脉络。比如一段只有十秒的哼唱,哪怕噪音盖过人声,系统也能判断演唱者当时的情绪状态??是思念?是悲痛?还是希望?”